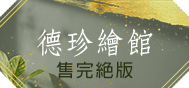- 您好,歡迎光臨萬達盛 ‧
- 會員專區 ‧
- 我的購物車 ( 0 )
- ‧ 購物方式
- ‧ 徵稿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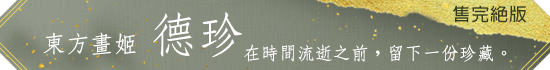

- 首頁 >
- 好書翻一翻 >
- 那樣的女子

書名:那樣的女子 / 作者:伍婈
故事簡介:
不服來戰!
早在他踏入辦公室的第一天,歐辰逸就感覺得到那曼娃對他有很明顯又很大的敵意,原因無它,就她以為勝券在握的行銷部副總寶座突被他空降大屁股坐去了,她心有不甘又苦無從抗議,有次偷偷在背後向人訴說他的不是被他逮個正著,害他一時氣不過,撂狠話之餘,咻咻一封戰帖就朝她飛了去。
她也有種,夠大膽,二話不說,面不改色,咻地一手接下戰帖,臉上盡是你這草包咱等著瞧的囂張氣焰。
結果咧,就說人不能太囂張,妳看看、妳看看!妳那曼娃輸得多難看,慶功宴上沒對他說出任何一句祝賀語也就罷了,還當著他的面借酒澆愁、出言不遜,迫使他不得不開始動用福利。來,當初說好的,輸的人要接受對方三個要求,他的第一個要求很簡單,就是,來、來、哩來,晚上來我家,到我床前……窗前,我歐辰逸絕對讓妳吃不完兜著走!
兩人果真吃不完兜著走,眼見梁子愈結愈大、仇愈結愈深,他有意緩解,她完全無視,虧他在她失業不得志期間好心地說要養她,卻遭她無情打槍,甚至連「請當我女朋友」這種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才說得出口的話,她都白癡似地聽岔誤解了,不分青紅皂白狠狠訓他一頓,君子自重,好自為之。
為何無論他怎麼努力取悅討好奉承阿諛巴結威脅利誘,她都無動於衷、依然故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討厭他、拒絕他、不理他呢?教他好生哀怨,好想不顧一切先把她撲倒再說。無奈,時機不對,只嘗到一點點塞牙縫都不夠的甜頭,手手就被咬得破了好幾個洞……
可惡!老闆的兒子是那麼好得罪的嗎?戰俘就要拿出戰俘應有的態度,而不是反僕為主,一天到晚欺負凌辱他啊!再這樣下去誰咬誰舌頭可就難說了,他一野獸起來是完全沒有道德尺度可言連他自己都害怕的唷,若想以身試法,來呀來(招手、拍椅子),儘管來!我歐辰逸隨時脫光光……坐端端等妳!
但是,那樣的女子,那樣的高傲,那樣的沒血沒淚,那樣的心似鐵打,如果她那麼善解風情好商量,他就不會總是遊走在抓狂的痛苦邊緣了。
誰來救救他……
主要人物:
●歐辰逸:從小被父親嚴格訓練培養為事業接班人,黯淡的童年生活中,唯一的慰藉與樂趣就是聆聽姊姊為他念床邊故事。
●那曼娃:出生在陰盛陽衰的家庭中,成長過程看盡爺爺重男輕女的嫌棄臉色,促使身為長女的她,養成不輕易服輸的強勢性格。專注自身成就,對男女感情的事很遲鈍不靈光。
●歐習誠:歐能企業大老闆,同時也是嚴厲的父親,老謀深算,公私分明,對兒子歐辰逸有很高的期望。
●沈釗:微茲集團董事長,優雅美麗,精明能幹,喜替家族晚輩物色結婚對象。
●夏毅濤:沈釗的二兒子,微茲集團總經理,英俊瀟灑,為人風趣幽默,有點少根筋,偶爾會做出損人不利己的蠢事。
●夏朵朵:夏毅濤的妹妹,感情外放又主動的女生,從少女時期即慕戀歐辰逸。
●歐辰安:歐辰逸的姊姊,性情溫和委婉,是歐辰逸從小到大的精神支柱。
●韋至凡:歐辰安的男朋友,在歐辰逸與那曼娃的感情之間扮演著深具影響力的重要關鍵角色。
●那茉娃:那家五姊妹中的老三,戀愛史豐富,自認情場高手,鬼點子一堆,堪不堪用倒是隨機不一定。
●小朱:歐辰逸的鄰居,熱心的年輕人,平常負責接送那曼娃「上工」。
內容試閱:
失算。
把她踢走,根本一點好處都沒有。
拉開百葉窗簾,透過玻璃牆板,歐辰逸望著隔壁那目前無人進駐的辦公桌椅。
實在很懊悔自己當初出手太狠,條件下得過於嚴苛。
讓她稍稍領教一下他的厲害就好,讓她知道他不是虛張聲勢就好,幹嘛非得逼她下台,趕她離開公司呢?
如今沒人與他抗衡,沒人隔著玻璃牆偶爾跟他大眼瞪小眼無聲無語的對峙,這樣上起班來顯然少了很多趣味。
昨晚她念的故事,他不確定是不是從他家書櫃上抽出來的任何一本書。
怪力亂神的內容,若非看著她念書時的唇形變化是那麼美麗生動,而她又愈念愈順口,教他很難插嘴,再加上睡意漸濃使不上力,不然他肯定跳起來跟她研討一番,希望她念的窗邊故事最好能以溫馨感人或詼諧幽默的內容為主,畢竟睡覺要儘量保持好心情才是健康人生啊。
嗯,不如這樣,今晚叫她早點上工,兩人針對往後讀物內容,面對面好好討論溝通一下。
念頭興起,他立刻撥了那曼娃的電話。
「喂,你有事?」正走在人行道上的那曼娃忙不迭地從手提包裡拿出手機,滿心以為是應徵工作的公司通知錄取或什麼重要訊息,結果一看來電者是歐辰逸,她的鬥志和語氣陡然降溫。
「喂,妳態度可以再差一點。」是有那麼不耐煩他,竟用那種沒半點溫度的口吻問候他,好傷人。
「什麼事快說,我等重要電話,你別占線。」是啊,整天整夜都在等所謂的重要電話,等到花兒都枯了,月兒都隱了,鳥兒都朦朧了,依然等不到半個聲影。
「晚上請妳吃飯。」
「沒事請我吃飯,有詐。」興趣度──零。
「沒事就不能請妳吃飯?」對他而言,有事沒事都可以請她吃飯,只要她肯賞臉,一天到晚請她吃飯都沒問題。
「我很忙。」誰有空給他請吃飯。就是有,她也不願。
「在忙什麼?」
「總不像你那麼閒,到處打電話請人家吃飯。」那曼娃輕翻白眼,語氣十分不耐。
「我哪有到處打電話請人家吃飯!我只請妳吃飯,而且是好意請妳吃飯,妳不肯賞光就算了,有必要對我那麼冷嘲熱諷嗎?」
「喔,多謝你的好意,我心領,但不去。另外,我絲毫沒有想對你冷嘲熱諷的意思,我講話本來就這樣。」要跟她交流,他最好習慣她的快人快語。
「少來!妳只有對我講話才會這樣。」她對別人都好得很、客氣得很,獨獨對他不屑又超沒耐心。
「呵呵呵。」那曼娃的假笑聲聽起來怪裡怪氣,「歐先生你別亂扣我帽子,我對誰都是一視同仁的和氣親切呢!」
「套妳一句話說,小心咬舌頭。」他才沒有亂扣她帽子,那是他經過長時間觀察所得到的真實結論,她當然可以否認,但他就是那樣認定她。
「我從不咬自己舌頭。」
「都咬別人的就是了?」拾人牙慧,他很滿意有這句現成的台詞用來反擊她。
「歐辰逸,你是坐上副總寶座就換了腦袋,還是真閒得發慌沒事打電話騷擾我、尋我窮開心?我跟你講,我沒空跟你抬槓!」那曼娃顯然被激怒。
「不管爬上什麼大位,我歐辰逸的腦袋始終是一顆聰明又真誠待人的好腦袋。那曼娃,妳是吃了炸藥?我只不過想請妳吃頓飯,兩人一起討論一下妳昨晚念的那本書而已,結果妳竟然不分青紅皂白攻擊我的腦袋,殺傷力是要不要那麼強?」見了誰都不殺,就獨獨殺他歐辰逸,他何其榮幸!
「想討論,晚上十一點我就一秒不差飛到你面前報到,你急什麼?」
「不然妳到底在忙什麼,說來聽聽,解我好奇心行不行?」歐辰逸悻悻然地發問。他就急著見她一面咩!這樣也顧人怨,他多冤哪。
「哈!歐少爺,謝謝你呢,拜你之賜,我現在可是標準道地的無業遊民,我在忙什麼,不就忙著『另謀高就』嗎?」
說來晦氣,堂堂七年業務行銷資歷,這該是多麼專業與實力兼具,偏偏這陣子來只獲得寥寥無幾且不痛不癢的面談。
連之前常說想把她這麼優秀的人才挖去的那些老客戶大老闆們,看來也都只是隨便說說,沒一個真心。她數次積極主動發出轉戰訊息,履歷投了又投,他們倒個個裝聾作啞,直接無視,從未有過正式回應。
唉,乏人問津至此,她想著想著都要開始自卑自怨兼自暴自棄了。
「喔,那曼娃,千萬別妄自菲薄,至少妳每晚替我念窗邊故事,我有支付工資,生活方面理應不無小補?」
「最好你那微薄的工資補得了我痛失副總寶座變無業遊民的巨大損失。」
「哎呀,妳這樣講,我不就罪過罪過了。」她對他,當真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懷恨在心、恨之入骨啊!
「豈敢豈敢,您歐大爺好身手,我願戰服輸,甘、拜、下、風。」什麼甘拜下風,她其實想一刀劈死他!
「好啦!衝著妳說出甘拜我下風這句話,我也不是小氣之人,對妳更不可能吝嗇,這樣啦,我、我──」
「你、你怎樣?」不是伶牙俐齒很會辯?這下吞吞吐吐是哪招。
「我養妳啦!」說得好像他痛下了一個多麼艱難的決定。
「什、麼?!」聞言大驚,那曼娃將手機拿離耳朵,盯著手機螢幕,一臉見鬼的驚嚇,幾秒後再重新放回耳邊,提聲罵去:「歐辰逸你神經病!」
「我怎麼就神經病了?」奇怪耶,他釋出最大善意竟換來她一句神經病。
「不然我還表揚你?」
「表揚是不必,好歹說聲謝謝,不行嗎?」
「我有手有腳還有一顆好頭腦,需要你養?」汙辱人也別這樣!
「失業期間,讓妳吃穿看我,我這樣好心卻被妳當驢肝肺,情何以堪。」他的心淌了好大一灘血。
「我沒把你的好心當驢肝肺,我只當你、是、驢!」
「喂!愈罵愈過火了喔妳!」竟把他這生得俊俏、長得挺拔的堂堂一表人才好男兒當成驢,這女人八成社會化不成功,損人話語說得特別溜。
「我沒有罵你,我是定義你。」
「那曼娃!」忍無可忍,歐辰逸終於對著手機大吼,他相信如果此刻她就站在他面前,他肯定二話不說縫了她那張嘴……
喔,不,是一口咬斷她的舌頭!
「晚上十一點見。」彼端歐辰逸氣急敗壞,臉色其差,那曼娃則因逞了口舌之快兼氣勢難得占上風而整個心情大好,頓時連失業陰霾都淡去不少。
掛上電話,漫步在街頭,她笑得可燦爛了。
※
「謝謝你,小朱。」
車子一在歐辰逸住處門口停下,那曼娃總是習慣且有禮地向小朱道謝。
小朱是歐辰逸相熟的鄰居,是從事藝術創作的自由工作者,由於那曼娃替歐辰逸念窗邊故事的時間是在夜晚十一點至十二點,基於安全考量,歐辰逸特別雇請時間運用較具彈性的夜貓子小朱當專門負責接送那曼娃的司機,以防她落跑或上下班途中發生什麼危險,一兼二顧,他考慮得可說十分周到。
「不客氣。啊,那小姐,我差點忘了!」就在那曼娃纖長玉指即將往門鈴按下時,小朱突然跳下車來,「哥說他今晚有重要應酬會晚點回來,讓我把鑰匙交給妳,請妳先進屋去等他。」小朱將一串鑰匙遞上。
「喔,這樣?」那曼娃稍顯遲疑地接過鑰匙,嘴裡道著謝,心裡想的卻是──既然歐辰逸沒空,怎不直接放她假就算了,還讓她進屋等,是要不要這麼麻煩,他一晚不聽故事不至於失眠吧?
何況應酬者九成會喝酒助興,他喝多了回來還能不直接倒頭睡下?
好啦,反正那個人怪癖特多,搞不好喝醉了反而睡意淡薄,非得聽故事才入得了眠,她就勉為其難等一等他。不過,等,沒問題,如果十二點鐘念故事的結束時間一到,他卻還沒回到家,那她定要立馬走人。
對準了鑰匙孔,在轉動鑰匙時,那曼娃望著那串以一身長約莫五公分、穿著件黑色小套裝、頭上高高挽著一顆又大又圓的整齊包頭、面部表情非常嚴肅的大眼睛娃娃當裝飾的鑰匙圈,不禁秀眉輕皺,粉唇微微一撇,冷笑。
什麼品味!
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拿個迷你娃娃當鑰匙圈這麼陰柔。
她低嘖了聲,進到屋裡,時間剛好走到十一點。
雖然主人不在家,她仍習慣一頭往他的臥房走去,動作流暢地在窗邊二人座沙發坐了下來。
沒了那人的說話聲,沒了自己的朗讀音,空間變得有些過分安靜。
她拿出手機,開啟音樂匣,讓美妙歌聲流瀉在無聊等待的時光中。
「咳,我回來了。」
「啊?」從場景模糊的夢中驚醒,那曼娃被趨近的高大身影及朝她俯首的俊顏給嚇了好大一跳!
「我回來了。」歐辰逸又說了一次,略帶酒味的氣息輕噴在她臉上。
「喔。」她迷茫地應了聲,欲將不知何時躺平的身子坐起,可他不偏不倚擋在上方,使她難以挪動分毫。
「睡著了?是找工作太累了嗎?」他今晚其實沒有什麼重要應酬,遲歸只不過是做為對她下午惡劣拒絕他邀約的一種無傷大雅且不著痕跡的報復。
「是等待令人累!」他的臉靠太近了,她不免帶著戒備把寫著疲倦的臉兒往旁撇去。「以後有事直接放我假,別這樣折騰。喔,對,鑰匙先還你,免得等會兒忘了,害你找不到。是說你品味也真獨特,大男人用這麼可愛的娃娃鑰匙圈。」她在座位周圍摸索了一陣,將掉進沙發縫裡的鑰匙串挖出來遞還給他。
「妳覺不覺得這娃娃的外型很像妳?」
「怎樣?」仔細一看,鑰匙圈娃娃的衣著造型,跟她平常的裝扮確實挺像。不知他意欲為何,所以她不動聲色。
「這鑰匙串是為妳準備的,收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我不需要。」開玩笑,她又不是他的誰,怎可隨便收下他家鑰匙。
「妳會需要的,我不一定每天都能準時十一點回來。」
「那我就在外頭等,我不介意。」她硬是把鑰匙串塞回他手裡。
「真不收?」他臉上未有不悅之色,但語氣頗冷。
「沒必要。」那曼娃搖頭。
「如果哪天妳覺得需要了,跟我說一聲。」反正這串鑰匙就為她備著,他相信總有一天她會需要……他會努力讓她覺得需要。
「不可能有那一天的。」不熟就不熟,實不必拿鑰匙來拉近彼此的淡交情。
「好,既然妳堅持,我不勉強,不過要是哪天我又無法準時回來,而且不巧忘了交代小朱鑰匙,到時妳在外頭站崗餵蚊子,可別怪我。」
「你盡量準時回來不就沒事了。」幹嘛?想故意整她哦?
「哼。」他冷笑,未置可否地轉開話題,「現在就有勞妳再多待幾分鐘,我洗完澡再回頭來聽妳念故事。」
他終於站直身子從她上空移開,走往浴室的途中邊抽領帶、解襯衫鈕釦,一派輕鬆自然,完全不在意那曼娃在場。
「念故事……」剛剛睡到忘了時間,不知現在是幾點,她趕緊拿出手機一瞧,十一點五十九分,「啊,十二點,我該下班了!」
阻礙物自動移除,她當下整個人跳起來。
「妳不是灰姑娘,不必執著於午夜十二點鐘敲響就急著離開。」歐辰逸半回身,淡淡瞥視她,此際他的襯衫鈕釦全開,隱隱約約露出精實的胸肌,頓時讓極少有機會以如此近距離看見男性胴體的那曼娃看得兩眼發直。
「可是十二點是收工時間。」被那霸氣的身軀所吸引,那曼娃喃喃出聲,其實不確定自己講了什麼。
「我說了,就等我幾分鐘。」歐辰逸不厭其煩又清楚地交代一次。「怕我不付妳加班費?」
「那是兩碼子事。」該、該死,歐辰逸你能不能轉過身去,別讓那毛茸茸的厚實胸膛對準我的眼睛,簡直污染我純潔的心靈啊。
「妳的眼睛在看哪裡?」歐辰逸聲無波紋似沒什麼情緒,然而嘴角笑意卻又有著那麼點說不出的性感與邪肆。
「我什麼都沒看到。」被抓包,那曼娃旋即別開眼,只不過,眼不見為淨沒錯,可她的心還是噗通噗通亂跳。
該死的歐辰逸!身材那麼好怎不去當模特兒或鋼管猛男什麼的,幹嘛「撈過界」來歐能跟她搶飯碗,可恨的是,他還搶了個大贏!
「總之,等我幾分鐘,我去去就來。」歐辰逸不待她抗議,轉身快步閃進浴室裡去。沒多久,沖水聲嘩啦啦地傳出來。
那曼娃感覺有些暈眩,眼底殘留著歐辰逸性感身形的影像揮之不去已夠糟了,更要不得的是,她腦中還自發描繪起浴室裡那男人的沖澡示意圖……
正當她心煩意亂在空間裡胡遛瞎轉,然後決定偷偷開溜之際,歐辰逸恰巧洗完澡出來,帶著一頭濕髮及渾身未散的蒸騰熱氣,朝她步步逼近。
當然他不是裸體的,但只用浴巾圍裹下半身對她而言已經算是裸體了!
那該死的厚實胸膛再次正對著她,像掛了肥餌的勾一樣緊緊釣住她的目光。
他在她面前站住不動,搞得她連呼吸都小心翼翼。
「呃,我在這裡耶!你就這樣大剌剌走出來都不懂得遮羞避嫌?」他以身制人的畫面實在太養眼太刺激,那曼娃受不了,只好趕緊以聲制人。
「我一點都不覺得羞。」就是她在,他才有心情犧牲色相啊。
「你不覺得,我覺得。」露兩點還不覺得羞?道德尺度沒設限嗎?「你好歹避避嫌啊!」她氣躁地說。
「避什麼嫌,這裡又沒外人。」
「我就是外人!」她幾乎是用吼的了。
「妳不是啦。」他笑了笑。
「少跟我裝熟,這一點必要都沒有。」那曼娃沒好臉色地瞪他一眼。
「好。既然妳這麼說,我就不跟妳攀交情,咱公事公辦,妳快點念故事,我晚上喝了不少,很想睡覺,妳快點念完,我好快點上床!」
「那你怎不直接躺平睡下就好,還聽什麼故事!」那曼娃語氣中帶著強烈責怪,除了責怪之外,對他矛盾的言行還滿是疑惑不解。
「既定且必要的儀式,睡前不可少。」他沒亂說,其實他之所以喜歡並習慣睡前聽故事從來都不是為了助眠,而是他單純喜愛有人挨在身邊為他朗讀,以及雙方交流時那或奇妙或祥和,各種難以預料的氛圍與過程。
小時候聽故事是溫馨多於一切,大了還聽故事則多點懷舊心情,尤其現在為他念故事的人是那曼娃,更憑添了許多搔人癢處及動人心魂的曖昧。
他愈來愈著迷於這樣的情境。
「是喔!都你在說,都你有理,就不知在我倒楣成為你的戰俘之前,你的睡前儀式都怎麼進行,又是誰幫你進行的哦?」那曼娃既怒且不屑,無奈講不贏他,只好一屁股坐下,粗手翻開書本準備開念。
「我姊姊。」靜默許久,他低聲幽然道。
「妳的意思是之前都是妳姊姊為你念的睡前故事?」她剛只是犯嘀咕而已,並沒打算聽他解答,也不認為他會針對這個問題做回應,沒想到他這麼容易掏心,竟然有問必答,這算是她的「意外收穫」嗎?哈!
「是的,小時候都是我姊姊念故事給我聽。」
「喔,那……」他直言不諱,接下來她反倒不知該接什麼話才好,繼續聊?
「她離開很久了。」他自動說明,解去她眉間的疑惑。
「離開?是死……」死掉的意思?
「喂,妳別想岔了。她人在國外四處旅行,只是平常我們很少聯絡而已。」
「喔,是,是!嚇我一跳,瞧你神色凝重一臉哀悽,我還以為……幸好不是!」那曼娃鬆了一口氣,所幸他的姊姊健在安好,不然她幾秒前還帶著輕率戲謔的心態,未免太不敬。
「我只是很懷念小時候那些有姊姊陪伴的日子。我姊大我五歲,打從我出生那一天開始,她就隔著醫院育嬰房的玻璃窗為我念故事,等我出院被抱回家之後,姊姊更是每天每晚從不間斷地為我念故事。
「說來神奇,或許是因為有姊姊細心的陪伴與呵護,我爸媽總說我嬰兒時期表現非常良好,十分乖巧,就算偶有哭鬧也只要我姊出馬就必能搞定。
「在我人生的整個成長過程中,姊姊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並不亞於父母,每當我鬧脾氣不開心的時候,唯一能安撫我、使我冷靜下來的就是我姊辰安為我念故事的聲音了。」
情境驅使,歐辰逸開始幽幽講述他與姊姊密不可分的童年往事。
「呃,聽起來你姊姊很疼你。我是長女,底下只有一堆性格怪異……各異的難纏妹妹,無法體會有姊姊是什麼滋味。」
「兄弟姊妹多是人生中莫大的福氣,妳有『一堆』妹妹,挺讓人羨慕的。」若有像辰安那樣溫柔的好姊妹,來上十個都不嫌多。
「是。」因為妹妹多而被羨慕,這不是第一次,殊不知去世的爺爺對家裡清一色是女娃很有意見呢!「那,你跟你姊為什麼不常聯絡?」
「我姊沒有隨時掛網的習慣,也不喜歡講電話。通常我傳訊息給她,她也只負責收看,我往往收不到她的隻字片語。」他不介意姊姊的「已讀不回」,甚至習慣得很,只是內心仍多少有些失落。
「你姊姊其實打心裡並不喜歡你這個弟弟,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吧?」不然人在天涯,家書抵萬金,她連親弟弟的信息都不回一下,感覺有點冷漠。
「當然不是。」歐辰逸失笑否認,「她只是努力讓自己的生活簡單、思想淡薄,不願意再背負過多的人間情感而已。」
「哦?也包括手足之情?為什麼?」聽起來像是他姊姊遭遇過什麼人間悲劇,留下創傷後症候群似的。
「都說世上情關最難過,我姊雖然熬過情關,可是從此心也沉了、變了,似乎對什麼人什麼事都不再有太多熱情,包括對我這個向來疼在心底的弟弟,她都沒那麼重視了。當然啦,我已經長大成人,她自然不可能再把我當幼稚的小弟弟看著顧著了。」
「原來是因為情傷而遠走天涯。」這麼想不開,足見傷得很深。
這讓那曼娃回想起被唯一前男友拋棄的經驗,當時她剛進入歐能企業不久,幾乎整個心思都放在事業上,年紀又輕,對於他的離去根本沒有太大傷感,反倒是後來耳聞自己是當時的第三者,所謂前男友的移情別戀根本只是移回原先的女友身邊去,這才使她感受到被背叛的憤怒,除了憤怒還格外自責,怪自己怎眼睛沒睜亮,竟然成為破壞和傷害另一個女人的第三者。
所以,被情所傷到底有多痛,她未能深刻體會,但她確實嘗過被蒙在鼓裡、被從背後捅一刀的滋味。
「講到情字總是一言難盡的,對吧?」歐辰逸意味深長地瞟了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