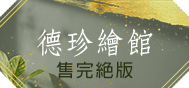- 您好,歡迎光臨萬達盛 ‧
- 會員專區 ‧
- 我的購物車 ( 0 )
- ‧ 購物方式
- ‧ 徵稿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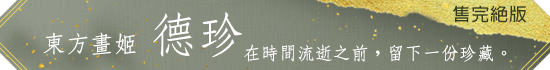

- 首頁 >
- 好書翻一翻 >
- 不單純小姐

書名:不單純小姐 / 作者:簡單艾
「喂。」單純閉著眼睛接手機,睏極的她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
若不是撥打電話的人比她還要有毅力,她根本不想接起來。
「不單純小姐,妳睡死啦,電話都響多久了!」
對方的大嗓門聽得她皺了下眉。
「我的大小姐,妳知道我這裡現在幾點嗎?」單純迷迷糊糊地看了手機上的時間。「早上四點三十五分耶,我們之間有很久的時差好嗎。」
「喲,這是在怪我嗎?」大小姐語帶嘲諷:「我們之間原本是毫無時差的,連一分鐘都沒有,是誰硬要跑到有時差的地方去的?」
「……是我錯了。」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大小姐聲音一軟,「明天打包回來吧,乖。」
「妳知道我目前都會待在這裡的。」不然她回國幹嘛。
「聽妳的意思是和鄰居處得不錯嘍?」
「漸入佳境。」可以這樣形容吧。
「漸入到哪個佳境?」大小姐可不是可以隨便唬過關的。「床上?」
「怎麼可能!」單純差點從床上跳起來。
「愛撫?」算……三壘?
「沒沒……」
「擁吻?」
「也沒……」單純覺得額際快要冒汗了。
「牽手?」
「這……」
「不單純小姐,妳真的愈活愈回去了!」大小姐聽不下去了,「人家都是年紀愈大愈不要臉,妳怎麼剛好相反?」
「……」
「十幾年前是誰邊掉淚邊發誓說,這輩子一定會好好照顧『他』的?結果呢?都當了兩個多月鄰居了,連牽手都沒有?妳不會是要告訴我,妳跟他連普通朋友都還稱不上吧?」
真準!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不單純,妳是在龜甚麼?」這次連「小姐」兩個字都省了。「如果妳還在顧忌那個妖言惑眾的甚麼『動情失去』理論……」
「一旦動情便失去。」單純替大小姐表達完整的句子。
「失妳的頭啦!既然這樣妳就不該當他的鄰居。妳看看妳那位鄰居,論長相、氣質、身材、學歷、工作、薪資,哪一樣不會讓女人睜大眼睛搶?近水樓台不動情?就憑妳那一點定力,得了吧!」大小姐罵人都不換氣的,「東西收一收,今天就回來吧,我派車去機場接妳。」
「……唉,大小姐,別砲轟我了,說說妳的目的吧。」單純連忙轉移話題,「一大早就被妳打擊得徹底了。」
大小姐停頓了下,好像在和別人說話。
「好吧,我也沒時間轟妳了,有人催我開會了,改天再找妳促膝長談。」
促膝長談?單純心中一嘆。是促膝長轟吧。
「說真的,我有件私事想拜託妳。」
「請說。」
「私事的意思就是不給酬勞,純粹拗妳做白工的。」
「我知道,不用強調。」單純沒好氣地笑了聲。
「有件命案,沒有證人,證據只有嫌疑人的自白,聽說已經委任律師了,但律師說必須找出強而有力的證據,否則很難洗清嫌疑。」
「喔,照片寄來吧,我看看能不能記錄下甚麼訊息。」
「寄了,限時專送,十分鐘前你們大樓管理員簽收了。」
「限時專送?」單純愣了下,「不是私事嗎?怎麼公器私用?」
「喂喂,不單純小姐,我們爭權奪利、拚死拚活、流血流汗爬到現在的位置,不就是希望能在私事上有公器私用的權力嗎?不然我們爬這麼高幹嘛,吃飽撐著?」
「……」要她說什麼好?
「再說了,妳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申請人暗中保護『他』多年,不也是一種公器私用?」大小姐掀底了,「不要跟我說妳一點私心都沒有。」
「……我很慚愧。」單純心虛了。
「慚愧甚麼?都跟妳說了這是我們該享有的權利。」
「是是,小的馬上去取件處理。」
「乖,麻煩妳加急。」
「幹嘛?認識的人的案子?」單純關心地問。
「我老媽的朋友的朋友的親戚,連一表三千里都稱不上的關係,我還要每天被奪命追魂CALL,妳說我急不急?」
單純忍不住笑了起來,她可以想像那樣的追殺畫面。
「唉,又來催我開會了,不跟妳說了,這事就拜託妳了。」
「妳知道我只能如實記錄,萬一……」
「廢話!妳又不是閻羅王,掛了。」
「噢。」手機一放,她閉著眼賴了一下床,然後才慢吞吞地掀被下床,刷牙洗臉換衣服,最後圍上一條圍巾、穿上羽絨外套、戴上手套,出門。
等電梯時,她還睏得閉著眼睛斜靠在牆上。
噹一聲,她沒有馬上動,還賴在牆上等電梯門打開,直到眼皮感受到電梯的燈光亮度才將眼睜開一咪咪。
「早。」
一陣風從她身邊飄過,有人從電梯出來時對她說了聲早。
「早安。」她有氣無力地回了聲,看也沒看對方一眼,進入電梯按下樓層後又懶懶地斜靠著打盹。
「單小姐。」
「嗯?」這是她下意識的反應。
「去買早餐嗎?」
「嗯。」單純心想,取完件後是應該順便買早餐的。
「買哪一家的早餐?」
「今天想喝豆漿。」天氣冷了,喝豆漿暖胃。
「麻煩妳順便幫我買兩杯無糖豆漿,兩個紫米飯糰,其中一個不要加蛋。」
「好。」
「妳重複一遍。」對方的語氣好像有點飄,帶著笑音。
「兩杯無糖豆漿,兩個紫米飯糰,其中一個不要加蛋。」
「很好,謝謝。」他鬆開撐在電梯門上的手。「去吧。」
「言瑾,那位小姐是?」官允知訝異地看著木言瑾與對方的互動,心裡有些不悅。
雖然兩人間的對話平常,也沒有親暱的肢體動作,她卻嫉妒了。
她認識的木言瑾從來不會麻煩別人幫忙處理私事,尤其是買早餐這種私事中的私事;更讓她無法接受的是──木言瑾說話的樣子。
那語氣透著輕快,神情帶點溫柔,話語間的用字遣詞毫不拘謹,自然得像老朋友一樣。
而她這個稱得上是老朋友的人卻不曾聽他這樣對她說過話。
「隔壁鄰居。」木言瑾開了門讓官允知先進去。
「那房子何時賣掉了?」她一直想當木言瑾的鄰居,卻總是找不到屋主談價錢,沒想到竟然已經有人搬進去了。
「不知道。」
「那她搬來多久了?」
「兩個多月。」
才兩個多月彼此就可以這樣輕鬆談話?官允知心中警鈴大作。「你們好像很熟。」
熟嗎?木言瑾想了想,跟她相處確實不需要想太多。「也許是因為她是個怪人。」
「哈啾──」
取完件站在大樓門口的單純摸了摸鼻子,轉頭張望了下,該不會有人在她背後說她的壞話吧?
自嘲一笑,聳了聳肩,她依照計畫買了想吃的早餐後,速速打道回府。
「單小姐,買這麼多早餐,有客人哦?」
管理員的寒暄讓她步伐一頓,瞪著一手一袋的早餐,懵了。
她這個人沒什麼大毛病,就是沒睡飽時會有點小迷糊。
是誰託她買早餐?她是答應了誰?
她跟大樓住戶幾乎都是點頭之交,唯一比較有交流的就是她的鄰居木言瑾了。
是木言瑾嗎?
那個總是要她先開口找話聊,爾偶才回她一兩句的人,會託她買早餐?還一次買兩份?
她從一樓想到十八樓,想到走出電梯,最後只好硬著頭皮去按電鈴。
如果不是木言瑾託買的,她今天三餐就都是豆漿加飯糰了。
門一開,率先映入眼簾的不是木言瑾的身影,而是玄關那一雙裸色的三吋半高跟鞋。
那雙高跟鞋她看過,跟向木言瑾告白的女人穿的一樣。
人都帶到家裡來了,還說不是女朋友!
突然間,一股莫名的不滿從心中滲了出來……她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拿著早餐的手一輕,清冷的聲音已響起:「還真買對了,謝謝。」隨即她手裡被塞進一樣東西。「不用找了。」門已經重新關上。
她怔怔看著手裡握著的一百元,呆了五秒鐘。
「泥馬的,我還倒貼二十五元!」
不用找?
這男人到底會不會算術?!滿腦子只記法律條文,所以連基本的算術都忘了?
因不滿而起的火愈燒愈旺,燒得她渾身發熱,回身將電梯用力一按!
不回家了!她要去頂樓吹風消火!
電梯門關上的同時,木言瑾再次開門。原以為應該還可以在走道上看見單純,沒想到人已經不見了。
抬頭,他看著電梯不斷往上跑的樓層數字,將手裡的五十元硬幣放回褲袋裡,關上了門。
※
「我將灑了神仙水的棉花球塞入兩個鼻孔中,還在頭上套了一個大的透明塑膠袋。
今天和我來開房間的人有點擔心地看著我,問我:『這樣不會窒息嗎?』
我得意地告訴他:『塑膠袋有挖幾個小洞透氣。』
他點了點頭,開始脫衣服。
說實在的,我壓根沒想到這個每天跟我在線上一起拿著大刀砍怪的虯髯客,現實生活裡竟然是斯文白嫩的小鮮肉。
在約好的捷運站見面時,我的小老弟就忍不住站起來了。
只一眼,他就輕易激起了我的情慾,我興奮地想著,這次肯定要徹夜不眠了。
為了掩飾我的衝動,我將背包拉到身前擋在胯下,一路上走路的姿勢顯得怪異又彆扭。
他的皮膚白皙光滑,摸起來比女人的還要舒服。
原本就情慾高漲的我,加上神仙水如夢似幻的催情,我達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我知道我的身體激烈顫抖,我聽到像我的又不像我的呻吟聲,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高潮時會叫得這樣淫蕩,像個女人一樣。
我好像興奮得暈了過去……」
單純的表情有些困惑,剛要按下錄音停止鍵時突然被人握住手腕,往後一扯。
來人握著她手腕的力道不小,但這一扯的力道卻不大,只是讓她順勢半轉過身體,面對對方。
「木先生?!」單純瞪大了眼,攻擊的手刀堪堪停在他的脖子旁,相距不到一公分。
收手,她任他握著她的手,隨著他的目光落在剛剛被掃落地上的照片與信封上。
照片上的男人臉色鐵青,全身赤裸,頭上套著一個透明塑膠袋,身體呈現蹲姿般的蜷狀,右半邊的身體已浮現屍斑。
木言謹撿起照片和信封,看著單純的眼神透著訝異與不確定。
這張照片他見過──在法醫的驗屍報告裡。
死者身高不高,體型削瘦,所以才能整個人被塞進行李箱裡,棄置在路邊的電線桿旁,等待資源回收的垃圾車收走。
嫌疑人已遭檢方起訴,相關的照片、報告,他還是以辯護律師的身分才得以翻閱。
而他的鄰居──單純小姐,不是檢方,不是院方,不是家屬,是怎麼取得照片的?
他靜靜地看著她,問題一個個從心裡冒出來,讓他一時間不知道該從何問起。
但最讓他吃驚的不是照片,而是她剛才錄音的一段話。
彷彿親臨現場的當事人,訴說著內心不為人知的祕密。
他聽過類似的情況描述,卻不及她剛才說的仔細與真實,詭異的是之前對他敘說的還是他的委託人,這次命案的嫌疑人。
她到底是誰?
為什麼每次見她都讓他對她有一種新的想法與改觀?
她防身的動作很快,快到他只來得及看到她停在他脖子旁的手刀。
他深信若不是她認出他而停手,現在的他已經躺下。
那不是一般民眾學的那種防身術,而是特警或特務那種特殊單位才會學的高級作戰技能。
他很清楚兩者間的不同,因為小時候父親曾教過他。
「木先生,怎麼了?」單純將聲音放緩放柔,她不知道木言瑾的心境轉折,只訝異著他怎麼會上頂樓來,又怎麼會突然抓著她的手不放。
她看著他撿起地上的照片,難道……他和死者有關?和她剛剛敘說的事情有關?
他該不會就是大小姐說的案子已經委任的那位律師吧?這麼巧?
「臨終敘述師。」他定定看著她,說得肯定。
那語氣堅定得不容她反駁。頓了頓,她一臉無奈地認了:「噯,我明明說過我不喜歡那樣的稱呼的。」
※
門一開,單純被推了進去,而木言瑾則雙手環胸,將背貼靠在門上,守著唯一的出口。
她第一次進到他屋裡。
跟她想像的一樣,簡單卻有質感的北歐風格,簡潔中藏著一絲暖度,跟他的人一樣。
然後,她的眉頭一皺。
三吋半裸色高跟鞋竟然還擺放在玄關,這就表示鞋子的主人仍在這屋裡。
「木先生,你女朋友在家,我們改天再談……噢……」她用手壓著額頭揉著,驚訝地看著剛剛賞她一記爆栗的木言瑾。
「都說她不是了,妳的記憶力到底有多差。」
「噯,不是我記憶力差,是木先生沒說實話好嗎?人都帶到家裡來了,還說不是。」
「我也把妳帶到我家來了,那妳是嗎?」木言謹冷冷反問。
「我們清況不同,怎麼可以混為一談。」
「那妳知道我和她之間是甚麼情況嗎?怎麼可以直接斷言?」
「……」單純一時語塞。
怪不得呀!
怪不得會走上律師這條路,而且還做得有聲有色;他那張嘴還真不是普通的會辯。
「妳在腹誹我甚麼?」看她突然不說話,木言謹有此一猜。
她瞪大眼看他,連內心的OS都能被猜到,這人果真很適合做這種諜對諜的攻防工作。
「我只是在想你和她是甚麼情況。」當然是胡謅的。
「為何這麼好奇?」
「我怕自己不小心變成無知的第三者……噢……」她又吃了一記爆栗。他的力道不大,但痛的是她的自尊心。
「就妳這德行,也想當第三者?」
「木言瑾!」
「她在客房睡覺,妳小聲點。」他的食指往唇上一比。
「都睡到你家來了,還否認。」單純還真配合地降低了音量。
「允知通宵熬夜,有些法律問題想找我討論。」
「一大清早?」
「今天是早了一點,不過也差不多是我的起床時間了,便下樓去接她上來。」其實他也有點意外。「我看她精神不佳,要她吃完早餐後先去睡一下,晚點再談。」
「喔喔。」單純聽了聽,「那我不打擾她休息了。」說完就想推開門邊的他,閃人。
文風不動。
「客房隔音不錯,音量放低點就不會吵到她。」
「沒辦法,我天生大嗓門。」單純甜甜笑著。
沒想到他那雙漂亮的眼竟然瞪了她一眼。「我要妳剛才的錄音檔。」
「可以。」那本來就是為了這個案子錄的,多一個幫手,大小姐應該不會反對。「我馬上回去傳給你。」
這麼乾脆?木言瑾有些吃驚。「我還有其它事要問妳,妳坐吧。」
「不行的,我們是連『好』鄰居都稱不上的關係,怎麼好意思繼續打擾。」
「記仇?」木言謹挑了下眉,對這種事記性就這麼好。
「我只是有自知之明。」她伸手去推他。
「單小姐。」
「你看吧,我稱你木先生,你稱我單小姐,多麼生疏的兩個人啊,要談我們──」
「單純。」口一張,單純兩個字已自然地從他嘴裡滑出,「還是要我稱妳『單』?」
她的心不由自主地顫了下。
「木先生,沒想到律師也這麼能屈能伸。」
「只要能釐清案情找出證據還無辜的人清白,只是換個稱呼而已還談不上能屈能伸。」
「木先生……」
「言瑾。」他糾正。
「啊?」
「現在還稱我『木先生』就太見外了,對吧?單。」
他那一聲「單」喊得又輕又柔,帶點笑意,帶點戲弄,帶點等她出招的期待。
她卻聽得渾身一僵。
他喚她的聲音低啞中帶著磁性,是她最喜歡的嗓音。
看著眼前高大俊逸的他,她突然覺得大小姐說得沒錯,當他的鄰居好像不是明智之舉。
可是怎麼辦呢?
她答應過木大叔一定要救回他、救活他、保護他。
前兩項她做到了,最後一項她也一直守諾著,但現在情況有變,沒親自守在他身邊她根本無法安心做事。
但……倘若再繼續這樣接觸下去,她怕自己會忍不住……
「我能給的資訊都在錄音裡,其它的恕愛莫能助。雖然是『臨終敘述師』,但說到底也只是一個平凡百姓。」她聳聳肩,雙手一攤,「我先回去發給你吧,有不清楚的你再問我。」
這次她沒有推開他,反而握上他的手腕將他向前一扯,企圖將他拉離門邊。
突來的舉動成功地讓木言瑾往前一傾,但他隨即步伐一跨,手腕一翻,掙脫了單純的箝制。
見狀,單純揚起了唇,再次出手的動作比先前要快上許多。
不敢掉以輕心的木言瑾全神貫注地拆招。
就見兩人站在玄關處你來我往,又是拳又是腳的,互有攻防,互有消長,但一時間似乎誰也沒能贏過誰,因此兩人便一直處在玄關處。
過招愈久,木言瑾眸中的驚訝愈炙。
他習武多年,小時候是父親領入門,之後是自己有興趣,加上職業的關係,難免會有一些利益衝突或威脅警告,學著防身有備無患。
單純的招式靈活輕巧,是女性慣有的打法,而他則穩健沉著。
其實他很清楚目前兩人之所以會僵持不下,全因為單純沒有盡全力。
也對,兩人並非仇敵,不需要打個你死我活。
「言瑾,你們在……做甚麼?!」
話聲一出,單純與木言瑾同時停手,同時看向一臉訝異站在客房門口的官允知。
「我們……」一開口,木言瑾便愣了下。
交手的兩人,最後都使上了擒拿。
此時的木言瑾一手勾著單純的後頸,一手扣住她的手腕;而單純的膝蓋則頂在木言瑾的腰際,另一手抓著他勾著她頸項的手。
那姿勢,詭異又曖昧,上半身幾乎貼靠在木言瑾身上的單純,只要彼此稍稍一動就可能親上對方的頰。
他連忙鬆手,而她又剛好推開他,一鬆一推之間,眼看她將重心不穩地摔出去時,他又反射性地去撈她的腰。
碰!是兩人一起摔跌在木地板上發出的聲音。
一時間,鴉雀無聲……
「噗哧!」單純忍不住地噴笑出聲來,一想到剛剛兩人幼稚的舉動便笑得直不起腰來。
她沒有聽見木言瑾的笑聲,不過在他紳士地扶住她的背幫她坐起來時,她看見了他抖動的肩膀與盈眼的笑意。
「言……」官允知走向前想扶木言瑾一把時,堪堪定在了原地。
只見木言瑾自然地抬起食指點了點單純的額頭,用著官允知不曾聽過的溫柔聲音道:「真是敗給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