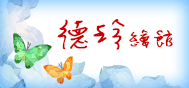- 您好,歡迎光臨萬達盛 ‧
- 會員專區 ‧
- 我的購物車 ( 0 )
- ‧ 購物方式
- ‧ 徵稿園地


- 首頁 >
- 好書翻一翻 >
- 諸子宴

書名:諸子宴 / 作者:栗和
這一夜,李玦心亂如麻,躺在李玦身側的墨成寧很快發現她的不對勁。
「大嫂,可是哪裡不舒服?」她起身憂心忡忡地看向翻來覆去的李玦,伸手探向她額頭,卻是一片濕涼。她心下一驚,趕緊起身點燈。
她立在床邊,柔聲道:「不舒服要和我說一聲,要是大哥知道了肯定怪罪我。手給我。」
李玦柔順地伸出皓腕,墨成寧往上一搭,輕聲道:「大嫂,妳思慮太過,損傷心脾,因而心血不足,血不養心……」她認真地低聲叮囑她,輕輕拍了拍李玦冰冷的掌心,未料李玦忽地手掌一翻,扣住她右腕脈門,一股炙氣注入,她右手登時痠軟無力。
「成寧,對不住了。」
墨成寧大為驚駭,不及細想便用左手掏出貼身銀針往李玦手背一刺,李玦吃痛放開她。
墨成寧急奔至房門口欲奪門而出,尚未拔開門閂,便被李玦用含光劍擋住去路。墨成寧一咬牙,抄出今早才買的貼身匕首,格開李玦的劍。
「為何要殺我?」墨成寧才擠出這些字,出招便稍緩,差點被刺中,只得凝神接招。
兩人在忽明忽滅的燭火中交手顯得綁手綁腳,李玦顧忌荀非和余平,不敢有太大聲響,只得加速出招,不讓墨成寧有機會嚷嚷。墨成寧心一橫,隨手撒了一把帶麻藥的銀針,便持匕首貼上前去。李玦哪裡肯讓她接近,含光劍劍勢在墨成寧面前形成一道光牆,將大多數銀針擊擋下來,又踏著蓮步避開剩餘銀針。
墨成寧見她露出破綻,迅速欺上前去,卻是中了李玦的計。
「撤!」李玦輕喝,手如游蛇般拂過墨成寧腕間,墨成寧忽感一陣痠麻,匕首便落下了。
她向後一躍,眨眼間,李玦劍尖已指在她咽喉上。
「成寧,我就是這樣一個貪心的女人。我不想負了師哥的愛,也不想讓袁大哥怨我恨我,對不住了。」劍尖顫動,語氣堅定。
墨成寧怒道:「妳將我殺了,好讓大哥不知道妳心裡早有了別人,卻要他一輩子癡等著妳!妳好狠的心!」
李玦心一緊,長劍匡啷一聲落地。看著地上閃著寒光的含光劍,只覺連長劍都在冷眼嘲笑她的失敗,雙腿一軟,便滑蹲下去,「哇」一聲哭了出來。
墨成寧正想踩住長劍,才發覺剛剛急於逃命,不及穿鞋,連忙縮腳。幸而李玦再無動作,她趕忙走向李玦,抄起地上含光劍以防李玦又發難。
「妳待如何?」墨成寧強壓下餘悸,冷靜問道。
「袁大哥他……寧可等不到我,甚至我死,也不願知道我背叛他吧。」李玦哽咽道。
墨成寧想了想袁長桑的為人,咬著下唇默認。
良久,李玦方緩緩道:「動了殺人滅口的念頭,對不住。」
墨成寧神情複雜地瞅著李玦,只見她一臉慘白,一副要自盡謝罪的模樣,心中又是苦又是惱。
她前些日子向荀非表白,雖然心知自己的想法是自欺欺人,但她卻無法遏止地想,倘若她成全了這對鴛鴦,上天會不會也憐憫她而成全她?
她腦中浮現上回在絕響谷溪邊,這對神仙眷侶相處的模樣。
她不斷說服自己,拆散這樣一對愛侶會遭天譴。心中唸著唸著,一雙杏眼也逐漸蓄滿淚水,因她明白,袁長桑又多了一個背叛者。
她仰頭硬生生收回淚水,淡聲道:「大嫂……」又立即改口道:「李姑娘……妳走吧。」墨成寧拋下長劍,抿緊發顫的雙唇。
李玦一愕,不可置信地看著她。
「妳勸他忘了我吧。」李玦長嘆道。
墨成寧低著頭,低聲而清晰地道:「我此番來尋,只見到李玦牌位。李玦已死多年。」
李玦呆了片刻,隨即心下感動,曉得她是在向自己保證會讓袁長桑死了這條心,便抄起劍擊斷腕上玉玦。她還劍入鞘,道:「這玉玦,原本是我死後才要取下的。」
她將兩段玉玦輕放桌上,又放上當初定情的木芙蓉銀簪,正色道:「李玦受墨成寧之恩,無以為報,請受我一拜。」便跪下去,磕了一個響頭。
墨成寧嘆了口氣,她實在說不出「好好生活吧」、「祝你們長長久久」之類的好聽話。
「保重。」語氣不輕不重。
李玦又作了一揖,抓起早就收好的行囊,離開客棧去與張輝碰面。
荀非與余平正在一樓木桌旁小酌,余平貪杯,已醉得不省人事。荀非今早在驛站接到家裡來的信,信中百般催促他歸府,說是石家要脅荀家再不提親,石家便要物色其他女婿人選,至今還拖著純粹是來自石家小姐的堅持。
都已訂了親,還恐生變?
荀非再看一眼信紙,字裡行間皆是復仇的迫切性和對他的期望,他冷冷一笑,卻是自嘲,接著按例將信紙探入油燈引燃,丟進碗裡燒盡。
荀非醉眼朦朧間,見一黑衣女子奪門而出,不久,便聽到噠噠馬蹄聲,竟就在這月黑風高的夜晚走了。
他心道:那身形……好似李玦。為何離去?墨姑娘知道嗎?她沒事吧?
想到此處,他驀地打了個激靈,醉意也去了七八分。他撇下趴睡得香甜的余平,跌跌撞撞地衝上樓,直奔長廊底墨成寧和李玦的房門前。
正待破門而入,荀非動作戛然而止。
萬一他方才看錯,那人並不是李玦,而兩人現在正安安穩穩地睡在床上,他這般破門而入會被當登徒子吧?
想了想,他仍決定必須確認墨成寧的安危,他敲了敲,裡頭無動靜,便伸手推門,訝異發現門竟沒上門閂。他心知有異,當下更急,逕自入室。
「妳沒事吧?」
墨成寧杵在窗邊發愣,一雙美目幽幽瞧著張輝與李玦離去的方向。她沒注意到荀非入房,因此被他的聲音給嚇了跳。
「荀公子!」淚珠險些滾落。
荀非繞著墨成寧細看數回,終於舒了口氣。
「沒事就好。」
微弱月光下,墨成寧木著一張沒有血色的臉,雙眼瀅然,彷似抱著她的肩一搖就能滴出水來。荀非藉著三分酒意,一股衝動欲摟她入懷,他伸出右臂輕抓她左肩,另一手按住她背心,墨成寧微微張大眼眸,軟著身子任他擺弄,孰料荀非左掌才碰到她背心,便如同碰到熾鐵一般縮回了手。
這個擁抱,有太多含意,他給不起。
墨成寧並無驚訝或失望之色,經歷李玦一事後,天大的事對她來說也如塵埃微末了。她淡淡瞥荀非一眼,輕聲道:「我放她走了。李玦已死,江湖上再無此人。」
墨成寧面無表情,像是灰心到了極點,只遙遙看著窗外,為姑姑墨平林的單戀、袁長桑的長相守候哀悼。姑姑自情場失意,便埋葬了她原有的嬌憨淘氣;袁長桑對李玦的癡愛更是深深烙在墨成寧腦中,九年如一日,天天惦念著她,這樣的袁長桑,若知道與李玦永生無法再見,天知道他會被痛苦折磨成什麼樣?
墨成寧想著家人的事,荀非卻怔怔瞧著她。這樣淡漠的小臉,比之憤恨哭泣更教他心如刀割。
「夜深了,你回去歇息吧。我明天便隨你上京醫治楊芙。」
荀非嘆了口氣,柔聲道:「妳也早點歇下來。」走到門口,又折返脫下袍子披在她身上,道:「要去外頭散心的話我可以帶妳去,宵禁什麼的不用管。」
墨成寧單手捂著將落未落的青袍,回眸給了他一個極清淺的笑容。「我想去屋頂吹吹風。」
荀非見她終於有了些表情,欣慰笑道:「小事一樁。」便推開窗,右手搭在墨成寧腰間,帶著她縱上屋頂。
「還記得我姑姑嗎?當年聽了你的笛聲而落淚的那個女子。」
荀非想了片刻,嗯了一聲。
「她愛著我大哥,大哥愛著李玦,李玦卻愛著鬼清。老天爺怎地如此殘忍?」
「莫要灰心,世上相愛如李玦與鬼清的不在少數。」他寬慰她道。
她美目瞟了荀非一眼,瑣碎地揀些姑姑和袁長桑的事告訴他。荀非靜靜聽著,偶爾插上一兩句,如此這般竟也說了大半夜。
「咚──咚!咚!咚!夜防賊盜,關好門窗!」更夫宏亮的喊聲自街道彼端遙遙傳來。
「四更天了,也不知李玦他們倆行至何處了。」墨成寧抱著膝蓋,把頭埋進雙臂間。
「他們?」當時他醉意正盛,只留意到有馬匹,卻不知還有另一人。
墨成寧點了點頭,悶聲道:「我在二樓瞧得分明,張輝早替她備好馬。」
荀非沉吟道:「張輝城府頗深,他相信我們是李玦的朋友,眼神卻洩出防備之色。替我們指路,卻似有其它用意。」在官場混了那麼多年,他欺人,人欺他,入耳的話往往要打折扣,在半真半假中,他自然練就一雙識人的利眼。
「咱們畢竟是外人,他多防著些也是自然。不過……我直覺張夫人是個真誠之人。」她露出一隻眼睛,瞇眼一笑。
「墨姑娘,張夫人那日究竟帶妳去灶房說了些什麼?」聽她提起,他若無其事地問道。
墨成寧將頭埋回膝上,囁嚅道:「她勸我順著自己心意。」
荀非好笑地看著縮成一團的墨成寧,揚眉道:「自己心意?」
她頰泛桃花,顧左右而它:「時候不早啦,再不睡就要天亮了。」
見她羞怯怯的模樣,他隱約猜到和她表明心跡有關。
荀非握了握拳,思忖著是該早點答覆她。
墨成寧抬起頭,見荀非別開了臉望著遠方。從側面看,他稜角分明,烏亮頭髮在頭頂挽了個簡單的髻,近日的奔波讓他更顯清瘦。
她滿足地欣賞著他,嘴角微微一翹。袍上濃濃的酒氣,揉合著芝蘭香,讓她一陣頭暈目眩,忍不住攏了攏肩上荀非的袍子,湊上鼻間輕輕一嗅。
荀非回過頭,恰對上自己的袍子──以及袍子上方露出的半張小臉。
墨成寧放開袍襟,尷尬一笑,迅速站起身,拍著裙身心虛道:「走啦走啦。」
荀非看了她一眼,默不作聲地起身帶她回房。
行至門外,荀非忽地轉身喚道:「墨姑娘。」
墨成寧正要掩上門,聞聲又開了門,歪著頭疑惑地望向他。
荀非暗裡又握了握拳,逼著自己平靜道:「我還欠妳一個答案。」
墨成寧看著他悽然的神情,腦中嗡的一聲,讓她瞬間白了臉。
她飛快掩起門,急促道:「改日再說也不遲,回京的路還長著。我累了,先去睡了。」
荀非一拳抵在門板上,額頭壓在拳上,盡量將聲音放柔:「墨姑娘,這事還是讓妳早點知道得好。」
墨成寧惶然地靠在木門內側,緊閉雙唇。他會拒絕她在絕響谷碧巖前的請求,一直在她意料之內,可她就是不願承認。
她太高估自己了,沒經過那樣的傷痛,她憑什麼要他放棄復仇?再怎麼易地而處,她仍是無法感受到砍在別人身上的切膚之痛。
墨成寧捂住耳朵,不願接受事實。到頭來,她依舊是一隻縮頭烏龜。
「對不住……」荀非的聲音帶著痛苦與歉意,低沉而清晰地傳入她耳中。
最後一絲想望破滅,利刃般的事實切割著她的心。她垂下雙臂,幽幽道:「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可為了達成那幾希處的仁義,要你放下身上的血海家仇……遑論你的家人,就是你,也沒可能答應的。你姓荀名非,荀子的荀,韓非的非,我想,你十年前就告訴我答案了。」
墨成寧澹然一笑,又輕柔道:「你甭道歉。無非是我太傻,換作是我,或許也會和你選擇走同樣的路。抱歉讓荀公子為難了。」
荀非默默聽著,再也按捺不住,欲推開門,卻發現她早已上了門閂。
「我沒事,但真的累了,明兒還要趕著上京不是嗎?」她艱難地說著,只盼他快些離開。
荀非深深望著木門,突然覺得它好沉好重。隔了層門板,卻像是隔著兩種不同世界。
「妳好生歇著,後日再回京城。」他轉身離去。
跫音漸遠,墨成寧緊靠門板的背一鬆,整個人滑坐到地板上。
今夜拚命忍著的那顆淚珠,終於啪嗒一聲,打濕襦裙一角。
她死命將身子縮成一團,額頭抵著膝蓋,壓抑地嗚咽起來。
「爹,對不住……我忍了九年,就讓女兒哭一次吧……」
新月光輝透過窗櫺微弱地包覆著她,使她顫動的身影看來格外淒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