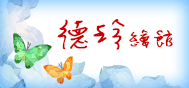- 您好,歡迎光臨萬達盛 ‧
- 會員專區 ‧
- 我的購物車 ( 0 )
- ‧ 購物方式
- ‧ 徵稿園地


- 首頁 >
- 好書翻一翻 >
- 日照蔚藍海

書名:日照蔚藍海 / 作者:裴甯
為什麼巴奈的媽媽會反對巴奈跟昭一爺爺在一起呢?
從林爺爺的敘述跟昭一爺爺日記裡的記載,紀海藍實在找不到答案。
巴奈的媽媽是來自南勢阿美族的傳統大社娜荳蘭社,就她查到的史料,娜荳蘭社一直都跟日本當局保持著不錯的關係,而且凱茵本人也在日本人家幫傭,會這麼反對女兒跟日本人交往實在令人費解。
「疑點重重啊……唔!」紀海藍自言自語到一半,就被列車高速過彎的震動給打斷。
「紀小姐,妳沒問題吧?」坐在她身旁,照例正以筆電處理公事的淺見時人淡淡的聲音傳來。
「喔,沒事沒事,我現在不會暈車了。」紀海藍回頭朝他一笑,內心有點暖。
是的,他們又在往花蓮的火車上了。
本來淺見時人說搭飛機就好,他不介意那個價差,只求平安舒適。但她覺得火車其實很方便,兩個小時就到了,還不必提早報到跟過安檢,在火車上可以看書或使用電腦,時間反而更好利用;再說火車站的交通位置也比機場方便,這樣加總一算並不會比飛機慢多少。在她一點一點分析給淺見時人聽後,他終於勉強同意,讓她訂了跟第一次去花蓮時一樣的普悠瑪號。
其實,他是不希望她跟第一次一樣大暈車吧。
紀海藍眼光轉到自己腳上的帆布鞋。自從她腳受傷之後,之前搭配OL風打扮的淺跟鞋當然不能再穿,但穿球鞋來配實在違和感很重,在她正煩惱該怎麼穿搭時,就接到淺見時人的E-mail,跟她說之後的打扮舒適整齊就好,以不增加她的膝蓋負擔為原則,她從此恢復自己習慣的休閒穿衣風。
與淺見時人相處了近一個月,紀海藍開始明白他隱藏在冷淡面具後的體貼。
越是明白,就越是在意,在意他把自己禁錮在過去裡。
自從知道他是雅憶姐的兒子之後,她就常忍不住猜想著他到底有一個怎樣的童年,才會型塑成現在的他,好幾次都差點要問出口。
她雖然是因為對「人的故事」有興趣才跑去念歷史,可是之前她有興趣的都是早就或快要進棺材的人,這是她第一次對跟自己同世代的人感興趣,連她自己都覺得有點反常。
是啊,真反常……是從上次他醉倒的那一次開始的嗎?不,也許是那個停電的晚上吧,又或是更早之前?
總之,心情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改變了。
他似乎也變了一點點,雖然還是冷冷淡淡,但已不再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
紀海藍悄悄觀察他的穿著。
時序進入五月,台灣各地都熱了起來,他終於脫下厚重的風衣,但依舊是一身筆挺黑西裝加上領帶規矩地繫在頸上。
好啦,有進步,至少現在不能再叫他風衣男了。
「紀小姐,有什麼想說的話就直說。」終於受不了她的注視,淺見時人停下手邊擬到一半的台灣支社下半年度銷售企劃書轉頭看她。
「欸……」被抓包了,紀海藍只好趕快轉移話題:「喔……那個,淺見先生,我們今天是跟馬耀大哥約在市區的日式料理店,不會有什麼您不習慣的東西出現,也不會灌您酒,您不用擔心。」
「我沒有說我擔心。」
淺見時人幾乎嘆氣。自從上次醉倒後,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好像變得異常嬌弱,這讓他非常無奈。
他早就下定決心,以後不管誰來勸酒,他都不會喝。
他不想再經歷一次那種無法控制,將自己赤裸裸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感覺。
雖然她跟他都很有默契地不再提那一晚的事,但當他隔天早上在家裡茶几上發現那杯沒喝完的蜂蜜綠茶時,就明白那一切不是他的夢境。
那一切都是真的,包括他想留下她的心情也是。
他上次談感情是六、七年前,還是學生時期的事,因為他先出社會而與對方的價值觀漸行漸遠,自然而然結束了,後來工作忙,他便沒再想過這方面的事。
他來台灣才將滿一個月,新工作很忙,再加上幫爺爺找人就已忙得人仰馬翻,上次偶然撞見那個好久不見的「母親」也搞得他有點煩躁……
總之,他還沒準備好讓自己再掉入一段感情,而且也討厭公私不分。
更重要的是,他沒打算談異國戀,他不想重蹈父親的覆轍。
綜上所述,他的結論是:無視這份不知何時萌芽的心情,繼續維持現狀。
可是這個女人真的常常在考驗他忍耐的功力。
他早發現她有發呆時猛盯著人看的習慣,而這習慣最近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就算他再怎麼擅長擺出一副淡定的態度,一直被如此「熱切」的目光凝視著,他內心當然不可能平靜無波。
所以說,爺爺派他來台灣,根本是來修行的,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
想到等一下又要與那位愛亂認表妹的餐廳老闆見面,也不知道過分熱情的他會不會又做出什麼令自己或令她困擾的事,淺見時人就覺得頭有點痛,只好勉力忍下嘆息,命令自己專注於面前的銷售企劃書。
※
「海藍小姐,好久不見啦,這裡這裡!」
兩人才剛踏出計程車,馬耀爽朗的聲音便中氣十足地傳來,他獨自站在只以日式拉門上一塊藍布低調標示店名的日式料理店門口。
「海藍小姐,我mama吃不慣日本料理,今天就沒帶他來,我們先進去吧。」
簡單的寒暄過後,馬耀領著兩人進了內裝相當具有日本風味的日式料理店,服務生帶他們坐進半開放式的包廂,送上茶水跟菜單。
點完餐,紀海藍起頭寒暄。「馬耀大哥,不好意思還要你放下餐廳的工作特地來市區一趟。」
「不會啦,我們做這行的,偶爾也是要四處觀摩一下。」馬耀環顧店內的裝潢一圈後,目光掃過淺見時人,最後一臉關切地落在紀海藍身上。「欸,你們上次回台北以後,日本人先生真的沒怎樣吧?他上次那樣醉倒真是嚇死我了。」
「還好啦,哈哈……」回想起當天淺見時人幼兒化的樣子,紀海藍忍不住笑出聲,發現鄰座的他正看著自己,才連忙拿起茶杯喝茶掩飾笑意。
「沒事就好,不然我原本有點擔心妳一個女孩子會不會被他怎麼樣。」
「咳咳咳!」紀海藍一口茶差點噴出來,嗆得眼淚在眼眶亂轉。「怎麼可能啊咳……」
看著她鄰座的淺見時人面不改色以最快速度遞紙巾給她的樣子,馬耀揚起一抹耐人尋味的微笑,決定很善良地不要去戳破。
「喔對了,這是我帶我mama去申請的戶籍謄本影本,不過上面好多日文,我有看沒有懂就是了。」馬耀從手邊的袋子拿出放在夾鍊袋裡的一疊戶籍謄本遞給紀海藍。「我還申請了光復後的,不曉得會不會有幫助,就當作給妳參考。」
「馬耀大哥,謝、謝謝!」
終於止住嗆咳的紀海藍接過夾鍊袋,馬上迫不及待地打開,抽出戶籍謄本影本仔細閱讀。
「JIRO.RAKO,昭和十三年三月三日生,RAKO.DAWA,大正七年七月十日生,DAWA.TIPOS……」紀海藍將戶籍謄本姓名欄上的片假名唸出聲,一邊在心裡換算著吉洛跟其母拉珂的年紀。
「嗯,這個是吉洛爺爺,這個是他的媽媽拉珂,而這個是他的外婆達娃,這一份是吉洛爺爺出生後記錄的。」
紀海藍為馬耀解釋了手上拿的第一份戶籍謄本的人名與上面記載的記事內容後,抽出下一份繼續閱讀;她的指尖追著一個個以毛筆寫就的片假名人名與出生日期,發現自己的呼吸因為興奮而急促起來。
「這一份是比較早的記錄,應該會記載所有達娃孩子的資料。」
「真的嗎?戶政事務所的人說,我mama可以申請他媽媽那一輩兄弟姊妹的資料,那應該是這一份了。」馬耀關切地微微前傾上身。
「淺見先生,我們是不是找對方向,就看這一份記錄了呢。」
紀海藍向身旁的淺見時人一笑,見他微微點頭回應後,便將以釘書機裝訂的戶籍謄本翻到第二頁,映入眼簾的名字讓她瞬間睜大雙眼──
「KAING.DAWA,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生!」
明治四十四年是西元一九一一年,換算到一九四四年盟軍第一次空襲時,這個凱茵就是三十三歲,而當時巴奈是十六歲,這表示凱茵是在十七歲時生巴奈,跟拉珂說凱茵十六歲私奔算起來正好時間相符……
「這個凱茵,應該是我們要找的那個巴奈的媽媽!」紀海藍掩不住興奮地跟淺見時人與馬耀各解釋了一遍她的結論。
「真的嗎!」馬耀興奮過度地伸手握住對座紀海藍剛放下戶籍謄本的雙手。
「嗯,馬耀大哥,真的是太感謝你了!」被難得有進展的喜悅淹沒的紀海藍,一時間並不覺得這姿勢有何不妥。
「紀小姐,服務生要上菜了。」淺見時人的表情跟平常看起來沒什麼不同,但聲音似乎比平常更沉了些。
馬耀先反應過來,立刻放開手。「啊哈哈,海藍小姐,不好意思,不知道為什麼,我聽到也覺得很開心就……哈哈。」
「啊,沒關係啦……」看著服務生把三人點的定食套餐送上桌,紀海藍才發現氣氛好像有點微妙。
紀海藍看著淺見時人以非常標準的持筷姿勢夾起放在小缽裡的玉子燒默默吃起來,連平常一貫會說的「我開動了」都省略,才確定他是真的心情不好。
怎、怎麼了?風衣……不,淺見先生的心情怎麼忽然就惡劣起來了?
「淺見先生?」實在忍不住,她開口喚了他。「怎麼了嗎?」
淺見時人緩緩將筷子放上筷架,右手長指圈上茶杯,似乎在壓抑什麼似地握緊又放鬆茶杯,最後才平板地開口:「我只是在想,即使證明了馬耀先生的家族跟巴奈的母親有關係,似乎也不能讓我們找到巴奈。」
「淺見先生這麼說也沒錯……」無法反駁淺見時人的評語,紀海藍前一刻還沸騰的興奮感瞬間被澆熄。
冷靜下來一想,戶籍謄本上根本沒有巴奈的名字,憑馬耀或吉洛爺爺旁系親屬的身分,依照戶政法的規定,也不可能申請到凱茵後來跟丈夫分家出去的記錄。
換言之,即使證明了親戚關係,他們也沒辦法循線追查下去。
不過,他們這個尋人任務本來就常處在線索斷絕的狀態,為什麼這次他心情會特別不好?
盯著淺見時人一如往常讀不出情緒的側臉,紀海藍實在理不出任何頭緒。
「咳咳,海藍小姐,妳的烤魚要涼了喔,趁熱吃吧。」被冷落在一旁有點久,將一切盡收眼底的馬耀,帶著惡作劇笑容開口打破那股奇妙的沉默。
「欸,對喔。」紀海藍自以為不著痕跡地收回視線,動手整理剛剛拿出的戶籍謄本放進夾鍊袋要還給馬耀時,忽然注意到奇怪的地方──
「馬耀大哥,為什麼吉洛爺爺光復後改的漢名,跟爸爸、媽媽還有外婆的漢名,統統都不同姓啊?」
吉洛爺爺叫「劉繼勇」,爸爸叫「張英樹」,媽媽拉珂叫「王來美」,外婆達娃叫「高德蔚」,要不是寫在同一張戶籍謄本上,誰都想不到他們是一家人。
「這在我們原住民的家族裡是很常見的事啦。」馬耀接過那一袋戶籍謄本,習以為常地笑了起來。「上次不是跟妳解釋過,我們阿美族命名的規則跟漢人不一樣嗎?光復初年的戶政人員不知道這件事,所以常常一個家裡面,每個人的漢姓都不一樣。」
「欸……」紀海藍驚訝得瞪大眼,忽然想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這麼說來,也不知道巴奈後來改成什麼漢名了耶。」
她之前完全沒想到這一層,開始覺得尋人的前途再次荊棘滿布。
「紀小姐,怎麼了?」見她眉頭少有地皺起來,淺見時人淡淡問了一句。
紀海藍向他翻譯剛剛跟馬耀對話的大意,淺見時人聽了,難得沒有皺眉還是嘆氣,只是一臉平靜地開口:「如果人有這麼好找,爺爺早就靠自己找到了。」
也許是漸漸習慣了這個小島上各種沒有規則的規則,他開始能夠淡然處之,不再像初抵時一點小事脫軌都能讓他煩躁不已。
「淺見先生……」他變得好淡定,跟剛來台灣時完全不同。
隱約覺得淺見時人似乎有哪裡表現得很矛盾,但紀海藍說不清究竟是哪裡,只能迷惑地盯著他出神。
「海藍小姐,不要太洩氣啦,至少巴奈真的是我們家族的人。」馬耀再度打破微妙氣氛,笑著開口安慰她。「雖然除了我爺爺吉洛之外,可能沒有其他知道巴奈跟凱茵的長輩還在世,不過我會再幫你們問問看的。」
「馬耀大哥,真的很謝謝你。」雖然沒能因此找到巴奈,但馬耀如此熱心的幫忙,還是讓她心懷感激。
「不用謝啦。老實說,我有一種你們離真相很近的直覺喔。」馬耀看著對座的兩人,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夾起一塊生魚片丟進嘴裡。「我的直覺一向很準的。」
「呵……是這樣嗎?」紀海藍順順自己的馬尾,不解馬耀的信心從何而來。
「淺見先生,那我們這週末該去哪裡尋人呢?」紀海藍有些喪氣地看向淺見時人如常鎮定的側臉,希望總是指揮若定的他能有好建議。
淺見時人盯著茶杯裡立不起來的茶梗浮浮沉沉,雖然他不迷信,但此刻真有種他們的好運已用完的感覺。
這麼快就遇到瓶頸了嗎?
尋人線索再度全面斷絕,下一站,他們該去哪裡找誰,才能更接近巴奈呢?
※
自從盟軍第一次空襲花蓮港的那天,日野昭一就越來越難接近他的戀人巴奈了。
據說是巴奈的母親要求的,總之,河間先生不再出借作坊的小書桌給兩人讀書,也不准他再以非客人的身分踏進萩乃堂,日野昭一又恢復成最初只能路過、在門外張望的狀態。即使店主河間先生不在,隔壁商店的井上太太也會監視著他,讓他很難找到機會跟巴奈說話。
隨著空襲越來越頻繁,戰局越來越吃緊,學生被動員去幫軍隊做「奉仕作業」的時間也越來越多,有時甚至一整個禮拜都不在校舍上課,每天早出晚歸,他跟巴奈時常連隔著店門見上一面都不可得。
在這樣的狀況下,日野昭一跟同學邱勝彥與林明寬都通過了台北高校高等科第一階段的資料審查,也接受了第二階段的體檢、口試及筆試。
在兩階段的入學審查之間,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台灣徵兵制度」開始施行,凡年滿二十歲的青年男子都必須參加體檢,日野昭一等人剛滿十八歲,幸而不需參加體檢。
而後,一月底,台北高校高等科的錄取結果公布,同樣通過第一階段審查的他們三人之中,只有林明寬考取。正當日野昭一與邱勝彥共商落榜後的規劃時,邱勝彥也接到一紙錄取通知──但發通知者是帝國海軍。
一切起因於數月前海軍志願兵徵召時,邱勝彥曾被師長半強迫填寫「志願書」並參加考試,豈料竟通過篩選,三月底自花蓮港中學畢業後,必須即刻入伍至海軍服役。
「邱君,要活著回來。」
在邱勝彥入伍送別會的當天,日野昭一特地跑去南園村參加了,在一片武運昌隆的祝福聲中,他的心情無比沉重。
「嗯,日野君,你也要保重。」身著一身筆挺軍服,肩披縫滿街坊祝福「千人針」的邱勝彥,看好友比自己的表情還沉重,故作輕鬆地說道:「我一定會回來的,春香說我活著回來的話就嫁給我,我怎麼能不回來?」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有了這個理由,你游也會游回花蓮港吧。」日野昭一明白好友的心意,也故作歡快地回答。
此時,邱勝彥的表情卻忽然轉為嚴肅,他以日野昭一從未見過的認真表情直視他,低聲開口:「日野君,你要做好隨時會被徵召的心理準備,現在兵源極度不足,南洋戰場一天到晚傳來全員玉碎的戰報,為了補充消耗的兵力,聽說本土已把徵召二十歲以上男子的規定更改為十九歲,念文科的學生也都被徵召去『學徒出陣』,照這樣看來,把所有青年男子拉上戰場是遲早的事。」
「我明白。」
在好友邱勝彥跟自己一同落榜、卻立刻接到海軍徵召通知時,他就明白,曾經被師長半強迫填了幾張志願書的自己,必定也難逃被徵召的命運,甚至奇怪自己怎麼還沒接到入伍通知。
「我知道我說這個可能太多嘴了,不過,趁還沒接到入伍通知前,你該好好跟巴奈談一談,不然有些話不曉得還有沒有機會跟對方說。」邱勝彥拍拍他的肩,長指往不遠處的數排香蕉樹一比。「我叫春香帶巴奈來了,她現在在那塊香蕉田裡等你,那裡沒什麼人會經過,你可以好好跟她說些話,把過去幾個月沒辦法說到的份補回來。」
「邱君……」哭很丟臉,可是日野昭一差點為了好友如此體貼的舉動掉下男兒淚,只好拚命咬牙忍住。
「好了,快去!我也要去跟春香道別了。」邱勝彥不耐煩地朝他揮揮手,轉身走向不遠處等著他的青梅竹馬謝春香。
看著兩個月前還一起參加升學考試的好友彷彿一夜間長大的挺拔背影,日野昭一有種恍如隔世之感,忍不住將此刻的心願喊出口:
「邱君,保重!我們都要活著!活著再見面!」
邱勝彥沒回頭,只是揮了揮手,然後他帶著笑的聲音隱約傳過來:「喂,謝春香,妳學一下人家日野君好不好,我也想聽到妳這麼說耶。」
「邱勝彥,囉嗦耶你,等你活著回來再說吧……」依舊倔強的聲音傳來。
看著好友與青梅竹馬一如往常鬥嘴的樣子,日野昭一揚起微笑,轉身往香蕉田跑去。
他們活在一個無法預知明天的年代,那麼至少,把握住現在這一刻,好好傳達自己的心意。
把不說出口會後悔一生的話,鼓起勇氣說出來。
他走進香蕉叢深處,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娉婷身影。
「巴奈小姐!」
「昭一先生……」巴奈那雙美麗大眼,也正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緩緩走近。
「對不起!」他在她面前站定,忽然將她緊緊摟入懷。「這幾個月,都不能去教妳念書,我台北高校的考試落榜了,我們一起去台北的夢想不能實現,對不起!」
從未與日野昭一有過比並肩念書更親密舉動的巴奈,因著突來的擁抱而有一瞬間的全身僵硬,但她緩緩抬起了手,輕輕揪住他背後的衣襟。
「說什麼對不起……又不是你的錯。」
他揚手撫上她絲滑如緞的秀髮。「妳母親還生妳的氣嗎?」
他感覺掌心中巴奈的頭輕輕搖了搖。「她只是說,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他鬆開擁抱,雙掌改握住她肩頭,望進那雙帶著憂愁的深邃大眼。「她有告訴妳為什麼嗎?是因為我是內地人嗎?」
從巴奈垂下的目光,他明白自己的猜測離真相不遠。
「她說了一些……關於我父親的事。說他的父親在代表社人與警察協調衝突時過世,懷著他的母親與社人被迫離開他們住的土地,日子過得很辛苦,所以留下了絕不能與內地人通婚的遺訓。我父親本人因為生計問題幫內地人工作,但心裡很排斥內地人,染上傳染病時因為不願意給內地醫生醫治而過世。我母親雖然對內地人沒有什麼仇恨,但因為她很愛我父親,所以決心要替我父親守住這個上一代的遺訓。」
巴奈重新抬起頭,一雙美麗大眼中有著堅決。
「我只希望昭一先生知道,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內地人裡有很壞、惡待我祖父母的,但也有像你跟河間店主一樣很親切、給我很多幫助的。如果我父親不要那麼固執以血緣來判斷人的好壞,那他今天也許還會在世;而我母親只因為你的血緣就反對我們來往,在我看來,就像我外婆因為我父親是敵對社的後人而反對他們結合一樣,並沒有道理。我的母親很頑固,但我希望她有一天能明白,就像她仍然決定與我父親結婚一樣,我對你的心意也不會因此改變。」
「巴奈小姐……」面前堅定直視自己的女子,美麗得不可方物,日野昭一覺得自己這一生再不會遇見比她更加美麗的女子,他動情地再度將她擁入懷。「我對妳的心意也一樣,不會改變。」
「巴奈……」他第一次捨棄敬語,用極親暱的語氣唸出戀人的名字。「我不久後大概也會像邱君一樣被徵召,如果我能活著回來,不管怎麼樣,我們都要在一起,好不好?」
「不好。」一向溫柔的巴奈難得語氣強硬起來,雙手緊緊摟住他的腰。
「嗄?巴、巴奈?」戀人的回答跟舉動強烈矛盾著,日野昭一傻住了,一顆心懸得好高。「不好的意思是?」
巴奈抬頭,索求承諾似地開口:「不管你去哪裡都要活著,答應我。」
第一次知道戀人也會有這種小小任性語氣的日野昭一愣了一秒後笑出聲。「好。那妳也要答應我,要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聽到空襲警報要馬上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不然每次空襲警報一響,我就擔心妳。」
巴奈點點頭,還想再說什麼時,便聽到香蕉田外傳來警察的聲音:「日野昭一!吉野村宮前聚落日野家的兒子,人在這裡嗎?」
警察大人找他有什麼事?
日野昭一毫無頭緒,但也知道怠慢不得,只好放開懷中的戀人,急忙往香蕉田外跑去。
「警察大人,我是日野昭一。」
一看到面前的陣仗,日野昭一心裡就有不好的預感。
除了見慣的吉野村派出所警察,還有兩名面生的軍官。
「日野君,你怎麼獨自跑來南園村,讓兩名軍官大人從你家特地跑過來找你!」警察劈頭就罵人。
「無妨。」其中一名軍官制止警察的喝罵,從軍服外套中抽出一張紙,開始宣讀:「日野昭一,恭喜你光榮地被選上海軍『特別攻擊隊』,即將為帝國盡忠!」
「什……」流進耳中的話語,將日野昭一的血液瞬間凍成冰。
特別攻擊隊,俗稱神風特攻隊,任誰都知道,一經出征,有死無生。
隱身在香蕉樹後將剛剛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的巴奈,只能用手死命摀住嘴巴,不讓自己的哭聲被警察跟軍官聽見。
才剛承諾要好好活著的戀人,下一刻便身不由己地打破了承諾。
※
「紀小姐,明明說故事的是我,怎麼哭的是妳啊。」在自家客廳中,年邁的邱勝彥停下說故事的節奏,好笑地笑了起來。
「邱爺爺,對不起……」紀海藍接過身旁淺見時人替她抽來的面紙,胡亂擦去眼淚鼻水。「我想到巴奈跟春香的心情,不知為何就覺得很想流淚,我平常沒有這麼愛哭的啦……」
邱勝彥跟淺見時人交換了一記束手無策的眼神。
「妳這麼愛哭,倒有點像巴奈。」邱爺爺忍不住取笑她。「可是她是以為日野君沒辦法活著回來才哭,妳明明都知道結局了,到底是在哭什麼意思的?」
「紀小姐,別哭了,邱爺爺跟我爺爺最後都還活著。」
被紀海藍的眼淚給淹得手足無措,淺見時人只好很笨拙地指出顯而易見的事實來安慰她。
這女人平常明明開朗到有些少根筋,卻在意外的地方很易感。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那張總是笑著的臉掉下眼淚,他會覺得很不好受,雖然仔細一想這女人哭得一點道理都沒有。
「唔,對不起,我知道……」紀海藍又擤了好幾次鼻子,才終於止住眼淚。「邱爺爺,不好意思,打擾您說故事了,後來怎麼樣了呢?」
「先說我自己吧。」邱爺爺抿了一口鹿野紅烏龍,才又繼續:「因為當時台灣聯外的航路都被盟軍封鎖住了,軍部也擔心盟軍會登陸台灣,我跟其他同期入伍的人在海兵團結訓後,沒被送去海外,而是被派到台灣各地駐守。我在高雄海兵團服役,命大躲過很多次轟炸,直到終戰一個月後部隊解散,才回到花蓮港。」邱爺爺以簡單幾句話將自己驚心動魄的戰爭經歷總結。
「那,我家的爺爺,又是怎麼活下來的?」淺見時人少見地開口追問。
他從不知道自家那個總是笑呵呵的爺爺居然曾是特攻隊隊員,不僅爺爺本人從未提過,那本爺爺交給他的日記裡也隻字未提;要不是他跟紀海藍因為不知該去哪裡尋人而再度拜訪邱爺爺,這段過去可能永遠不會被提起。
也許這是爺爺不願回憶的一段過去,但是,他想知道,在自己血液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這條血脈,究竟是如何倖存下來的。
或許自己也被身邊這個一說到歷史,眼睛就發亮的女人給影響了吧,他想。
「時人君,你現在這個認真的表情,還真像你爺爺年輕的時候。」
邱爺爺頗感懷念地微笑起來,又拿起紫砂茶杯啜了一口茶,透過茶湯氤氳的熱氣望著對座的淺見時人跟紀海藍。「用我這雙老花眼來看你們兩個,其實也滿像日野君跟巴奈的呢。」
聞言,微訝的淺見時人與鼻頭紅紅的紀海藍對望一眼,又連忙避開對方的視線。
是這裡的人喜歡把一起行動的男女當成一對,還是他們真給人這樣的錯覺?
這樣的想法無端竄入淺見時人的腦海,使他微感困擾地皺起眉。
「邱爺爺,我們不是那種關係啦,怎麼可能!」先開口撇清的是紀海藍。
「怎麼可能」是什麼意思?
淺見時人眉頭皺得更深,發現自己有種不太痛快的感覺。
「呵呵。」邱爺爺只是不置可否地又喝了口茶。「巴奈第一次被春香跟我撞見跟日野君在一起念書時也是這樣說的啊。」
「這是兩回事啦,邱爺爺。」紀海藍哭笑不得地回道。
這女人否認得也太快了,她真的這麼不願意跟自己扯上關係?
……不對,他在想什麼!他現在該問的不是這個。
「邱爺爺,您還沒告訴我們我爺爺是怎麼活下來的。」無視心中不受控的情緒,淺見時人決定讓對話回到正軌。
「呵呵,抱歉,這小姑娘的反應實在太有趣,我都忘了該回答問題。」邱爺爺笑著放下茶杯,跟他們大致解釋了他事後從日野昭一那裡聽到的故事。
「……原來如此,謝謝您告訴我。」
雖然早知是喜劇收場,但聽完故事的淺見時人仍不自覺地鬆了一口氣。
「不用謝,時人君,我只是把我還記得的事情告訴你而已。」邱爺爺搖搖手。「很抱歉我還是沒辦法告訴你巴奈究竟去了哪裡,日野君引揚後,我再也沒見過巴奈,後來我也離開這裡好幾年,回來的時候更是人事全非了。」
「等等……春香呢?」紀海藍略感困惑地開口。「邱爺爺,您回來了,那春香有嫁給您嗎?」
「小姑娘,妳很細心哪。」邱爺爺垂下眼,唇上的微笑有些苦澀。「但你們就算知道了春香的事,也是找不到巴奈的,我還是不說了吧。」
剛剛原本還很融洽的氣氛頓時因為邱爺爺的沉默而凝重起來。
淺見時人看出邱爺爺談話的興致已失,便禮貌地帶著紀海藍與老人道別。
「淺見先生,對不起,是我不小心問了不該問的問題。」一離開邱爺爺家,紀海藍便一臉懊悔地跟淺見時人道歉。
「沒關係,再聊下去,大概也不會有巴奈的新情報。」見她自責的樣子,淺見時人也不打算苛責她。
他本來就沒期望能從邱爺爺這再得到什麼有力情報,今天至少聽說了爺爺祕密的過去,已算是意外的收穫。
從爺爺那裡拿到的聯絡資訊已經全部用光,目前找到的片段線索也全部陷入膠著,他現在僅有的週末時間也容不得他做地毯式的搜尋,再加上爺爺不准他找徵信社代勞,確實是到了一個很難再有進展的瓶頸。
「那麼,淺見先生,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呢?」紀海藍仍帶點鼻音的問題傳來。
也許,某些謎團,就像邱爺爺充滿祕密的內心一樣,必須等待時機才能解開。
只是,在沒有新對象可拜訪的現在,暫時中止隨身口譯的委託,在台北等待進一步的消息,會不會對面前這個意外愛哭的女子造成困擾?
看著面前鼻頭仍像麋鹿一樣紅的紀海藍,向來總能迅速下決斷的淺見時人,第一次感到猶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