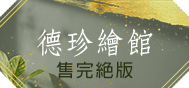- 您好,歡迎光臨萬達盛 ‧
- 會員專區 ‧
- 我的購物車 ( 0 )
- ‧ 購物方式
- ‧ 徵稿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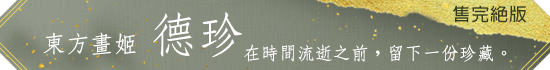

- 首頁 >
- 好書翻一翻 >
- 大月國師

書名:大月國師 / 作者:唯二子
第一章
大月國,夜晚。
圓圓的月亮掛在樹梢上,淡淡一抹浮雲遮在月亮前,不一會兒,雲濃厚起來,遮蔽了月光。無人的街道上,若不點燈,就會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闇黑中。
離皇宮最近的國師府,在管家傅梨的命令下,點起百盞燈籠,但今晚的夜色卻和府邸主人的心情一樣,灰暗深濃到難以照亮。
傅梨正愁苦著燈不夠,就接到主人歸來的消息,趕緊放下手邊雜事去迎接。
這幢宅邸的主人是當朝護國國師——司徒壇淵。
大月國的現任國君依賴咒術的神奇力量,大力擴建祭司處,在前幾任護國國師建議下,推行新法,命令每個孩子在出生十日內,都要接受祭司的占卜,一旦卜筮出孩子有靈能,便抱養到宮中,由祭司教導,培養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才。
司徒壇淵便是二十五年前由民間被抱養到祭司處的,且由於天生帶來的靈能太過強大,一開始便由老國師照顧,承襲老國師的姓氏,並蒙先帝賜名。而他也不負眾望,處處顯示過人天分,據說能力之強,能一人抵禦千軍;傳出去之後,各國不是急欲網羅他,便是想刺殺他。
司徒壇淵不悅地走下馬車,精怪幻化成的奴僕恭敬地從門口排成兩列,沿著長廊一直列隊到府邸深處。據府邸唯一另一個活人傅梨的說法——這是為了符合國師尊貴身分應有的排場,以及驅趕宵小、讓過度好奇的平民不敢接近的必要手段。
司徒壇淵走得很快,他邊走,一邊解開御賜的紫狐披風,像丟抹布一樣往旁邊扔。
傅梨伸出雙手,把價值不菲的披風穩穩接住,緊跟在司徒壇淵身邊。
「大人,您辛苦了。要先準備浴水嗎?」
「晚一點。」
司徒壇淵還是走得很快,身上紫色朝服的袍襬像波浪滾動,金線繡紋流動出華貴的光芒。
「派出去的妖精找到紫涯了嗎?」司徒壇淵那比起女子還要姣好的面容,此刻嚴肅地對著傅梨詢問。
「回大人的話,還是沒有小姐的消息。」
「是嗎?究竟躲哪裡去了……」
雖然整天埋首案牘之中已經有點疲憊,但司徒壇淵還是急著找尋司徒紫涯的下落。紫涯是老國師的獨生女兒,如果老國師逝世前沒有把他的祕密告訴紫涯、如果紫涯安分一點別想著對付他,那麼一切都會不同。知道紫涯握有祕密之後,他網開一面,沒有殺人滅口,只是把她關在家裡幽禁起來;誰知道她竟神通廣大到帶著他寶貴的護身符逃走。
司徒壇淵擰著眉。紫涯的居所遍布符咒,讓紫涯無法走出去;事發之後,他竭盡所能尋人,能用的方法都用過了,能想的也都想到了,她到底怎麼逃出去的?
「你把那天的情形再說一次。」
「大人啊,我都說過幾百次了!」
司徒壇淵用力戳著他的額頭,冷冷地瞪他一眼。
「要你說你就說,哪來這麼多話!肯定是你哪邊疏忽掉了,否則怎麼會找不到人?再仔細說一次,任何蛛絲馬跡都要回報。」
傅梨扁嘴。「大人,那天一大早,小豆芽先端洗臉水去給小姐,小豆芽聽小姐的吩咐,去換了一盆熱一點的水,再回去時小姐就不見了。那天您不也徹查過?什麼異狀都沒有啊。」
傅梨再講一次重複了幾十遍的話,已經有些不耐煩。這位主人雖然官從一品,是整個大月國唯一靈能強大到足以擔任國師的一位大人,但或許是跟在他身邊久了,太瞭解現任國師的底線,因此只要掌握他表情的細微變化,只擁有普通靈能的傅梨,偶爾也敢對他輕鬆說話。
「那棵豆芽說的都是真話嗎?」司徒壇淵面露兇狠,猶豫了一陣子,「把那棵豆芽煮了吧,如果豆芽臨死還是說一樣的話,本國師再試試其它辦法。」
傅梨愣了一下。司徒壇淵性情雖然挑剔,但是對府邸裡的精怪還算客氣,一向放任讓傅梨去管理,上下和樂融融。可是……煮豆芽?
「呃,您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不考慮。」司徒壇淵斜飛的墨眉底下,眼睛露出一絲紅光,周身也泛出冷意。「晚膳本國師要看見熟透的豆芽菜。」
司徒壇淵揚手,原本只是要摒退傅梨,但因為這個動作,袖子往下滑,露出了一截手臂。
他的右前臂有老國師為了壓抑強大靈能衝破他的身體而繪製的古老神咒,像紋身一樣,用黑色條紋勾繪的圖案是鳥,喙短、身圓、翼長、尾捲,唯有獸眼的地方是血般的鮮紅色,晶亮有神得彷若活物,盯視著膽敢注視牠的人。
咒紋只露出一瞬間,傅梨馬上移開視線。
不知是巧合還是真的有詛咒,凡是對這位國師不敬的人,都會在無意間看見他的右前臂,然後連連作惡夢或出意外。最讓人引以為鑒的就是福王爺;幾年前他惡意捉弄司徒壇淵,嘲笑他女氣又裝神弄鬼,硬是看了他的手臂,卻從此染病不起。
雖然司徒壇淵解釋過咒紋本身無害,但傅梨才不相信呢。國師小心眼又有疑心病,在咒紋上施咒可是最尋常不過的事了。他雖然想保護小豆芽,但誰曉得國師不是有意露出咒紋來警告他。
當天晚上,司徒壇淵如願在餐桌上看見一盤豆芽菜。
司徒壇淵擰著眉,無聲又帶壓迫地,用眼神詢問傅梨。
豆芽說什麼了?
傅梨被看得沒有辦法,苦著臉跳腳。
「都說小豆芽不知道嘛!您看我把她煮了,她也沒換其它說法呀!可憐的小豆芽,明明是信任大人您才來投靠國師府的……」
「知道了。」
司徒壇淵拿起筷子,往盤子裡夾了一小撮豆芽菜,牙齒咬斷豆芽的清脆聲響,在安靜的飯廳裡聽起來挺詭異。
「唔——」傅梨捧著肚子乾嘔。
司徒壇淵瞪他一眼,繼續食用豆芽菜。
「你在菜園裡找塊地方施肥吧,晚些本國師去施咒讓豆芽菜長快一點,以免小豆芽的精魄無處附體,讓附近吞食精魄的妖怪吃掉了。最近開雲城裡不太平靜,多了許多污邪的妖怪。」
「是誰說要煮了她的真身的啊!」
司徒壇淵停頓動作,揚眉冷冷看回去。
「你有意見?」
「我是擔心嘛!大人在人界已經惡名昭彰,只剩在精怪群裡還有點聲望,如果連這點好名聲都沒有了,我擔心您會每天耳朵癢,還要應付一堆詛咒。」傅梨邊說邊損他。
此時門口飄來一張木盤,停在傅梨身前,傅梨把剛燒好的菜餚都放上餐桌後,空木盤便浮飄回廚房。
食物很精緻,司徒壇淵貪好享受,吃的用的都是上好的。心血來潮想吃魚翅鮑魚,有魚精替他抓來;想穿綾羅,有蠶娘織好獻上來。生活過得比皇帝還尊貴。
他咬著剛上桌的美味醉雞,心情卻不是很美好。
「哼,該死的紫涯,如果不是她把紅玉偷走,本國師也不必重複給自己跟府邸施護身咒。每天光是基本的護身咒就要花半個時辰,累死了!」
「前幾年我就說您何不把紅玉一分為二,您還說用不著。」
「你是想說本國師太笨嗎?如果找得到龍子的眼睛、雲山大神的尿液,要做多少護符都沒問題,偏偏就是沒有!花了五年集結百種珍品才提煉出一塊小小的紅玉做為護符,本國師的智慧已經曠古絕今了,哪還能分成兩個再去削弱紅玉的力量?」司徒壇淵不滿地哼氣。
「欸,是小的無知,您別生氣嘛!來,大人您多吃點肉,好有體力幹活。我告訴您呀,接下來您有得忙了,城西桃花廟的千年桃花樹不開了,住持老和尚想請您去一趟讓樹開花;還有季醴將軍前天又喝醉吵著要找您,吐了咱們家門口都是穢物,真是熏死了!」
「那傢伙……就說怎麼這幾天他看見本國師都躲開,原來是闖了禍。和尚那邊你去回絕,沒找到紅玉前,本國師哪得空!」
「呃,但是我把錢都收了,我想老和尚誠意十足,大人您不會拒絕,已經答應了。」
「啊?」司徒壇淵瞪眼。
「總共三箱金條,還是您要退回去?」
「嗯。」司徒壇淵沉吟一會兒,眼睛亮了亮,「那棵桃花樹有花妖在,所以桃花廟才能成就許多姻緣,香火鼎盛。告訴老和尚,要本國師出手幫忙可以,但是香油錢要提撥給國師府五分,當作往後每年酬謝花妖的祭壇費用。」
「是。小的明天就去告訴和尚這個好消息。」
窗外,遮住月亮的浮雲逐漸散逸,銀華月色灑落,繁華的開雲城總算瞧得出些許輪廓。國師府邸一雙主僕,討論的話題延續到金庫還有多少擺放空間。
*
夜半子時,司徒壇淵沐浴淨身完,換上乾淨的黑袍,兩手手腕各綁一條白色綢帶,半乾半溼的頭髮披散在腦後,任夜風吹拂。
他來到府邸東北角落花園裡的觀星閣;觀星閣是八角形建築,六層高;他取出一把彎曲的黃銅鑰匙打開門,原本漆暗的觀星閣,在他踏入的那瞬間彷彿春喚大地似,整個甦醒過來。木質地板的紋路首先發光,像流水一樣,光芒從觀星閣門口的地板開始流動到四周,遇到牆壁再蜿蜒上爬,延續到天花板,直到整個室內的木質紋理全散發淡淡銀光,照亮閣內。
司徒壇淵走到第五層。中間的祭壇在地板上畫了符咒,圓形的咒圖直徑有五尺寬,最外圍的一圈是金色古老文字,第二圈是象徵地與水的三角與曲線圖形,第三圈是代表火與風的聖獸鳳凰圖案,最內圈用沉重的黑色畫上五角星。
他站在五角星的邊緣,光裸足尖踩過星星邊角上的圓點,每當他踩過一個點,便有光線從構成五角星的線條中衝出來,強烈的光束直穿入頂,當他踩過五個星角,空間中已經出現一個由光壁構成的區域。
司徒壇淵退後兩步,張口道:
「青生,出來,別睡了。」
他話一說完,光壁就劇烈扭曲抖動,接著在光壁的後面,隱約有個人形出現;隨著人形越來越清晰,光壁便慢慢暗淡,直到光滅,那個人才從飄浮在地板上三寸緩緩地落穩地面。
那是一個手持象笏,束髮戴冠,穿綠色深衣,披墨綠對襟禮袍的年輕男人。
男人張開柳葉眼,細長的五官與太過白皙的肌膚看起來有些不像人。
「召喚我來,何事?」細細的聲音有點悠遠,空洞又捉摸不定,彷彿隔著一層霧氣與人說話,如果不專心,會聽不清楚。
司徒壇淵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他的象笏上寫下幾個字。
「找到她。」
血紅名字從象笏背面滲透到正面,青生看著象笏上的名字。
「你應該能夠自己尋找才對。」
司徒壇淵有些煩躁。「你當我沒試過嗎?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就是感應不到她的氣息,連我在她身上下的追蹤咒也完全碎裂了。」
青生微微皺眉,又悠遠地道:
「知道了,會幫你尋找。」
「感激不盡啊。」
青生為他輕佻的態度皺了眉。「還是一樣,你應該為國多盡點心,這麼強的靈能,應該為民所用。」
「我明白呀,但在保家衛國之前,是不是應該先保住自身呢?紫涯帶走紅玉,等同把我的壁壘帶走了,你說是找她重要,還是我用這血肉之軀去護國重要?」
青生嘆氣搖頭,接著身體破成碎片,碎片落到地上,化為光影,融進地板的紋路裡。
司徒壇淵坐到地板上,苦苦笑出來。雖然靈能強大,但他已經快虛脫了。
「每次要見你,都很耗費體力啊,居然還不想幫我找紅玉……每天穩著防護咒就消耗掉大半靈能,哪夠應付大家的要求,還護國呢……」他爬到護國國師這一路上得罪很多人,每天每天都有新的詛咒在攻擊他,加上前幾年曾經中過黑巫術的招,身子大傷,不得已他才會做一個厲害的護符帶在身上。
知道他必須依賴紅玉的只有老國師跟傅梨。老國師臨死前又把他這個弱處告訴紫涯,現在他們一個死了,一個每天在他身邊,只要再除掉失蹤的紫涯,就沒人能威脅到他了。
「青生啊,快點找到紫涯吧,我可不想死得太不光彩呀。」
夜很深,司徒紫涯帶著紅玉消失,又增加了一個日夜。
司徒壇淵倒在觀星閣的祭壇上,陷入沉沉昏睡。
按照慣例,召喚青生以後,他會連續睡上兩天,這期間要是有強敵來襲,完全不知不覺,因此若非必要,他不會麻煩青生。
兩天過後,司徒壇淵張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青生給他的提示。
這次非常直接了當,是一張紙條。
青生是古老的靈,肉身腐朽後被某個術士鎖魂,只能停留人間,為術士所用。青生古老到已無法深究,承載數萬年的記憶,老古董的所做所為,經常令人費解,這次青生倒是學會大月國的文字了……
有一回皇帝請示是否要與草原民族打仗,青生給司徒壇淵的答覆是一顆西瓜。司徒壇淵不得已又把青生喚出來,相詢之下才知道西瓜要剖開見紅才能吃,所以是見紅收割的意思,可以攻打。司徒壇淵進行一次卜筮常常要耗費時間解讀結果,就是歸咎於青生給的提示太難以理解。
司徒壇淵捏著落在祭壇中央的白紙,上面是熟悉的青生的字跡,寫有司徒紫涯的下落。
——活著,但不在現世。
「活著,但又不在現世……」他糊塗了;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卻沒聽過有人能活著卻不在現世的。「到底會是哪裡?陰間嗎?」沉吟呢喃,實在對青生留下的答案很不滿,但是青生一向正確,眼下只缺成功解讀。
他努力想、用力想「不在現世」的意思。
古籍裡有記載能來去古今的精獸,精獸即便脫離現世,也還活著,那麼……人呢?
他靈光乍現,覺得這可能就是正解。但是紫涯是如何辦到的?
「紫藤花精?」他喚。
不一會兒,他耳畔就出現粗嘎的男子聲音。
大人?
「老國師逝世後,紫涯見過誰,你可知道?」
老國師交友廣闊,來弔喪的人多,小姐見過的人不下數百。
「真麻煩。」司徒壇淵不耐煩地來回踱步,走了三五回,才下定決心,速速找來筆墨紙硯,「反正也沒其它辦法,試試總比不試的好。你把紫涯見過的人都一一說清吧。」
是。首先是丞相焦玉官,小姐的未婚夫婿鄭之粲,黑袍祭司李寶清、樸寧順、白泰安三位,奶娘楊碧玉……李氏代理家主李嚴冬、觀相師韓遠……
司徒壇淵一個一個書寫,依序憶起當中幾位向紫涯問候的場景,都沒什麼異樣,但難說他們之中的誰,是否是幫助紫涯逃走的同夥。
小狼毫一頓,冬字第二點重重暈開;他提起筆,對這名字沒印象。
「這李嚴冬是誰?」
承夜國人,是小姐在承夜國的兒時玩伴。
「喔,是了,確實有個高個兒的異國男人。」他想起來了,那男人面生,印象中穿著黃褐袍子。
紫藤花精停頓了一下。
李嚴冬是位姑娘,您記得的那位是她的家僕。
司徒壇淵臉皮抽了下。他平常最好面子,此時不甚好看。「是麼?」
「是。」
「罷了,她家裡幹什麼的?」
老國師與小姐住在承夜國那年,小的在府邸裡從未移動,並不知情,對李嚴冬不瞭解。
司徒壇淵只覺得自己問了蠢問題。紫藤花精在國師府裡生根,老國師當年當然不可能把一棵樹挖過去。
「有誰會知道的?」
那一年老國師誰也沒帶上,恐怕只有青生大人才知情。
司徒壇淵擰起眉頭。
「這般神祕,可要追究清楚才行。」
*
承夜國朝廷推法實用,歷代君王不奉行鬼神之說,主要熱中算學、器械,因此李家代代相傳的堪輿算命營生向來生意清淡,只夠維持基本家用。
李家現任代理家主李嚴冬,為人謹慎,不苟言笑,人如其名,甚少與人交往,只有橙縣衙門的劉捕頭每隔一兩個月會來串門子。
劉至謙今天又上李家了。李家人對於代理家主與劉至謙每回密談都要耗上個把時辰早已習慣,只是私底下會忖度到底劉至謙有啥毛病,要請教這般久。
「嚴冬姑娘,妳說這犯人開鎖不竊,還在一天內連開城內四大富商的庫房,究竟是為什麼?」
李嚴冬一身黑袍,脂粉不施,淡淡盯著劉至謙帶來的「開鎖案」證物資料。
「我不知道。興許只是想鬧鬧衙門。」
劉至謙恨恨拍桌。「簡直無聊!」
「也或許,是四大富商的敵人不約而同在警告他們。」她看著描摹下來的四處鞋印;四個鞋印大小不同,鞋底的樣式不同,可以知道分別是出自啟羅號、老泰興、豐祥號三家鞋鋪。「有點奇怪,這些犯人的鞋子似乎都是近期購買的。」
「咦!」劉至謙靠過來,站在她後邊一起看著鞋印圖樣。「妳怎麼知道?」
「這鞋底有波浪條紋,是啟羅號為了防滑特製的厚黑靴,因為耐用又不怕雨天路滑,許多腳夫都穿這款式。條紋防滑的效果受人稱讚,所以這個月啟羅號在製靴底的時候,為了讓靴子更止滑,把條紋加了三條,總共二十三條。」
「這靴子是在一個月內買的。」劉至謙些微訝異,「一般要闖庫房的小偷會穿新鞋嗎?」
他自言自語居多,所以李嚴冬並沒有回答。
「再看這兩張圖,都是豐祥號的鞋;雖然大小不同,但從鞋底磨損不多看來,也是穿不到十次的鞋,說不定還是全新的。」她指節敲了敲描圖的右下角,「瞧,這裡黑了一塊,所以沒有鞋紋,表示有什麼東西黏在鞋子上了。依這東西的大小形狀,我猜是犯人還沒把店家黏在鞋底的標價拿掉。」
劉至謙聽完,急急翻出還沒講到的那張鞋印圖,看到了其中關鍵。
「有了!真的如妳所說,全是新鞋!」鞋底有製成年月,正是本月。「這犯人若不是同一人,肯定也是同夥。」
「大有可能。但詳情還得看了現場才能定奪。」
「妳要去現場?」劉至謙拔聲。
「不行麼?這回的犯人挺聰明,留下來的東西不多,光看這點鞋印,我也推論不出什麼。」她淡漠道,起身拿起掛在屏風上的黑披風,「走吧。」
「這就走?」
「您不得空,我自己去也行。」
說完,李嚴冬繫好披風,戴好帽兜,直接步出。
「嚴冬姑娘!」劉至謙三步併成兩步趕快跟上。「妳就不擔心犯人還在附近埋伏嗎?」
「犯人也有可能因為我們反覆追查而放棄作案。」
劉至謙翻了翻白眼,當然是趁她沒看見的時候。這姑娘斷案無比聰慧,但執拗也是一等一的。
「現在埋伏在旁也沒關係,反正早晚要入獄。」
「話不是這麼說的吧。」他有點無奈,還是緊緊跟了上去,保護她的安全。
橙縣有四大商,城裡好的地皮集中在城西、城北,這四名商人也居住於此,庫房建在隱密之處;四大商人出事後,城裡商賈人心惶惶,無不增加防備。
李嚴冬先到最近的黃姓商人的庫房。
劉至謙是橙縣裡極為盡力的捕頭,作案現場在他嚴厲要求與派人看管之下,原封不動保留了下來。
她在鞋子外面套上白布,走進現場。
離作案已過三日,犯人的鞋印卻還很清晰,似乎是作案前踩過了哪處泥濘。
她靠近庫房門前,蹲在地上審視腳印,照著腳印在旁走過一遍。
「怎麼樣?有無斬獲?」劉至謙問。
「這步伐太小了。按理說,有這尺碼的腳,身材應該也挺高大才是;但是這步距卻不大,跟我一個姑娘差不多。」她站起身,環顧四周。「可有派人看過屋頂瓦片?」
「瓦片?」
「嗯,派人去看看吧,或許會有其它證據。」
「好。」劉至謙很快叫來捕快,黃姓商人也讓奴僕搬來長梯,分頭派人上屋頂。
約莫半個時辰後,消息傳回來,說是東邊的屋簷上有腳印。
李嚴冬一聽,跟著去看,爬上去看過腳印後,知曉了大概。
劉至謙也一道上去,眼見稱奇。
「這也是犯人留下的?」
「不一定。但黃家這幾日沒派人修葺屋頂,會上屋頂來的,其心可議。」
「這倒是。」劉至謙揮手招來捕快,命令把屋頂上的腳印也拓下來。
黃家看完了,接著去司馬家、柳家、秦家,在這三戶也發現了印痕淺的腳印。
勘察完現場已近黃昏,劉至謙讓其他捕快先回衙門報告進度,自己送李嚴冬回家,路上繼續討論案情。
「屋頂上小的腳印才是真兇嗎?」
她點點頭。「是同一人作案。留在地面上的腳印是用來混淆視聽的,犯人刻意讓人往高大粗魯的漢子想,所以只要將留下來的證據往相反方向想,約莫就是犯人的真貌。」
「大就是小,男……就是女嗎?」
「此犯心細如髮,不無可能。」
李嚴冬腳下頓了一頓,直直看著眼前。
「這年頭姑娘也能犯案了呀……」劉至謙兀自感嘆,見她停在自家巷口,也跟著望過去。
一個年輕男子帶著一個小廝站在她家門前,男子的面容看不真切,但是一身耀眼的服飾,非富即貴。
「怎麼?認識的?」
李嚴冬搖頭。她不認識那麼招搖的男人。
「那就是客人了。太好了,又有生意找上妳。」
「是客人,但不是來卜筮的。」她一派無事地往前走,邊想著是大姊的債主還是二伯的債主;如果對方來意不善,她最好也強硬些,可不能給對方好果子吃,以為李家好欺負。
劉至謙再跟上。「怎麼知道不是來卜筮的?」
「若是,家裡不會讓難得上門的生意站在門口。」
「喔!」劉至謙恍然大悟,再看了眼那距離越來越近的「難得上門的生意」。「妳放心,有麻煩我必定傾力相幫。」
「不必。您回頭提醒縣丞大人把上回破案的獎金撥給我就好。」
劉至謙尷尬了。「妳先前硬是要我擔那份功勞,縣丞大人當我是同僚,近日公子娶妻,大人先把那筆獎金借用了去,我開口去要,實在有些為難。」
「當真是幫兒子娶妻嗎?」她呢喃。
「難道還有別的?」
「改日你去煙柳巷探探吧,別說是我指使的就好。」
「煙柳巷……」劉至謙呆了,那可是許多名妓攢了私房錢以後安置宅子的地方。
……